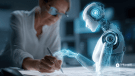懸在空中的人影以四分之一秒速慢動作緩緩降下,一名身材中等而且豐腴標緻的女人停在我面前,背對著厄洛斯他們三人。
我張大眼睛觀察她那垂落腰際的黑褐色秀麗長髮,如同頂級石膏凝結成的暗白色肌膚,明亮沉靜的黑色眼眸、英挺的鼻樑配上鵝蛋臉,天雕地琢的美貌幾乎令人忘記呼吸。她戴著一塊薄薄的面紗,穿著一襲潔白無瑕的連身長裙,上半身露出雙肩,及於鎖骨,裙襬則輕輕垂下,斜長曳地。尤其裙衩還開得老高,黃金比例的身體曲線在衣裙皺褶裡若隱若現,深深藏起肚臍以下完全沒有任何妊娠紋的光滑肌膚。
我還看見她右手拎著一顆蘋果,從她的纖纖玉指間透出幾道光采奪目又令人讚嘆的金色光芒。
她慢慢轉身,看向十餘步外的厄洛斯等人。
「母親大人!」「阿芙羅黛蒂!」「我的女神!」三人同時喊出聲。
我的老天鵝啊!這位將飽滿翹臀正對著我眼睛視線不到一公尺的美魔女竟然是愛慾之神厄洛斯的媽媽!那位總管世上一切愛情、美麗與性愛,司掌人間所有情誼的美神阿芙羅黛蒂 (Aphrodite)!難怪連出場都是四分之一秒速,我猜這如果不是家教就是遺傳。
「你這個做法不大正確唷,厄洛斯。」美神阿芙羅黛蒂開金口。她的語音跟外貌一樣美的出奇,我第一次親耳聽到這麼撫媚溫柔的娃娃音……簡直就是從電視裡走出來的志 0 姊姊。
「這是我唯一能做的,若要教訓這種不明瞭愛情真諦的凡人,照 SOP 走就對了。」厄洛斯看起來一副餘怒未消的樣子。
「你別忘了他是個已婚有家庭的中年大叔。那支黑色銀箭會讓凡人死亡,然後還得想辦法讓他重新復活,但是從遠古以來往返冥界的手續就很麻煩,你也不是不清楚。雖然他復活之後會再次像個孩子般底去對世界產生好奇,還有愛上某個特定的情人,卻會導致他拋下累積至今的種種因果與成就。所以即使能成功強迫他的靈魂洗心革面,對於他的妻兒並不公平。」她回頭以眼神餘光冷冷看了我一眼,我感受到快要結冰凍僵的恐怖寒意。
冷靜之餘總算讓我弄清楚剛才的狀況:搞了半天原來不是重開機 (restart) ,我是差點要被重灌 (reinstall) 啊!
「您說的對。抱歉,我一時衝動,沒仔細考慮那麼多。請母親大人原諒。」厄洛斯像個乖寶寶似的低頭向他母親道歉,但是剛才被黑箭瞄準的人可是我耶。
「那妳覺得應該怎麼辦才好?這件事從一開始就很棘手。」阿特羅玻斯上前質問。
「他是個聰明人。既然他已經差不多懂得了存在與愛情的本質,我覺得只要他願意認錯就夠了,剩下的問題由他自己想辦法處理。我們不需要為凡人想太多,而且我們自古以來就已經幫他們太多忙了。」
「有道理。」摩耳甫斯點頭贊同。「人類的慾望是個無底洞呀,不分晝夜都有人委託我入夢去假扮他們想見的人,簡直快忙死了。」
「委託人那邊怎麼處理?」厄洛斯問。
「這一開始就是非分之想,別理她就是了。任何超過自身能力與合理範圍的念頭都是妄想,不應該拿出來祈禱,也不應該接受請託。別忘記我們是最接近人類的神祇,不是整天拿著魔法棒死背咒語的黑巫師。我們本來就不是有求必應,也不會因為食言就發胖。再說,也許她一開始就應該直接去拜託赫拉 (Hera) 而不是我們。」
聽起來像是準備要吃案的樣子,妳自己不覺得這樣才是黑心嗎?不愧是「最接近人類的神祇」啊。而且她似乎對某女神有點不屑,我想是因為她擁有手上這顆寫有 καλλίστῃ1字樣的金蘋果……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句古希臘文?難道我忘記自己其實曾經學過嗎?
「沒錯唷,沒錯。」摩耳甫斯大力點頭贊成阿芙蘿黛蒂的意見,竟然還轉頭看了我一眼,不曉得是嘲笑我太胖還是有其他原因。我覺得他現在根本是個不折不扣的美女正確主義者,信仰美麗即正義,服膺標緻即真理的最高原則。
「如果沒別的問題就準備收工吧,你們先回去原地休息。我要跟他再交代幾句話,講完就讓他回去。」阿芙羅黛蒂發落指令。於是三人點頭領命,沒幾下就消失不見,只剩我和阿芙羅黛蒂留在現場。
她說有話要跟我講,現在卻站在旁邊直盯著我不發一語。我無心關注她那足以驚天動地的絕世之美,繼續皺著眉頭揉著發疼的腹部,目不轉睛底看著重現於眼前的小書齋,心想這可能是最後一眼的機會。
「你這樣不行。」阿芙羅黛蒂邊說邊走了過來,取下我繫在手腕上以神奇頭髮織成的莫比烏斯帶,輕輕一握就將它揉成灰燼隨風散去。
「他們果然沒有真正說服你,或者應該說…矯正你。」她先下了判斷,但我不認為有否認或反駁的必要。
「如果始終重複著迴圈,你的生命就會停留在這個時空,終生都無法開花結果。從來沒有人可以永遠待在母親的肚子裡,連神祇也不例外,必須從子宮裡靠自己走出來。」
阿芙羅黛蒂接著說:「你遇見她時還是個孩子,她卻已經是個母親了。她不願耽誤你,你卻辜負了她的期望,難道你還想辜負那些在現實生活裡等著你回家的人嗎?」
我開始流淚,過去從來未曾因這段往事流下的淚水,已累積了許多年。
「現在我要你自己親手毀掉這座小屋,你必須全程睜開眼睛做到結束為止。我只陪你做這一件事,就當是我對你未來人生的祝福。」
她主司人間情愛,但此刻卻冷酷無情底像是殘忍的死神,原來這才是她處理感情的態度。
「你可以流淚、哭泣或吼叫,甚至咒罵都行。但如果你閉上眼睛或是別過頭去,即使動作沒有停止,被摧毀的小屋仍然會恢復原狀,就像西西弗斯 (Sisyphus) 推著巨石那樣陷入永恆劫難。你必須想通前因後果,深刻覺悟後一次就做到結束,然後我才會讓你從這邊離開。否則你就會像普羅米修斯一樣,被我用鎖鍊永遠綁在這間小屋上,直到有人願意犧牲自己來解救你為止。」
我難道沒有別的選擇嗎?
「你可以開始了。」阿芙羅黛蒂面無表情底說。
但是我沒有任何動作,繼續看著小屋流淚。這間小書齋曾有一瞬間是我生命的全部,我不願毀掉它。它就是我初戀的紀念碑,是我生命中最純粹愛戀的墓塚,也是我迄今唯一願意葬身於此的地方。
這下子我完全明白為什麼後來會害怕山坡上的夜總會了。我怕因為死亡而永遠失去回憶學姊的能力,卻又不能讓有關她的記憶干擾我的日常生活,於是我不停底躲進重重腦霧裡反覆遺忘,努力去遺忘那些早該遺忘卻也不應遺忘又難以遺忘的傷心往事。
「你可以開始了。」她又催促了一次。
「我對那位 M 女士說過一句話」,我一手拭去半邊淚水,頭也不回底無視她的存在,問她:「妳怎麼覺得我會繼續相信妳?」
「那你認為可以做出怎樣的選擇?」她反問。
「我可以選擇生命裡最大也是唯一的可能性。」我暗自下決心,但已隱約浮現恐懼。
「死亡嗎?這就是你們凡人所能想出的最好答案嗎?」她輕輕鬆鬆就能看破我的想法,真不愧是最高段的奧林帕斯十二主神之一,但我認為這其實只是心理諮商的 SOP。
「死亡無法解決問題,只不過是逃到另一個地方去受苦受難罷了。若你沒有洗滌靈魂、淨化自己,未來陷入困境時依舊無解,卻只學會永遠逃避再逃避。若你不相信,可以試試看。」她露出一絲幾乎察覺不出的異樣微笑。
我當然懂她所說的道理,但我不相信也不願接受她操控我的生死。雖然選擇死亡違背了我的人生理念,可是我不願毀去我曾經存在的證明。
我知道問題的原因。自從失去她之後,我就開始自暴自棄,貶低自我的存在意義,牽拖出一連串藉口不去認清現實,否定我們之間的愛,假裝不曾存在過。最後才會被迫做出這種矛盾選擇。
對,其實我一直懂得,這間小書齋不但是在精神上守護著我的子宮,也是我生命中的潘朵拉之盒,留存著我在現實世界裡從未看見的希望──與她永遠相愛的唯一希望。
我打從心底厭惡這個對我毫無希望的世界,但不願憎恨與毀掉有關她的一切事物。我必須要停止回憶與思考才行,這已給我帶來莫大的痛苦!
於是我重重給了自己兩下耳光,趁自己受到衝擊的頭腦尚未恢復與回心轉意之前,在怒吼中一個箭步從頂樓向外跳出去。即使我進入永恆的睡眠,至少那份留存的希望還鎖在這世界的某處與她同在。
我察覺自己早已掉進情感構成的霧霾裡,放棄以理性思考尋求出路,寧願選擇傷害自我也要保護所曾深愛過的事物,還一廂情願底祈禱所有關愛我的人們最終能諒解我的愚蠢。
我天真底以為能死在自己選擇的地點,跟心中的缺憾同歸於盡,以為如此就能稍償夙願,假裝自己無憾也無懼。
最後我想起愛爾蘭作家、詩人王爾德 (Oscar Wilde) 寫下的一句話:"The mystery of love is greater than the mystery of death." 我閉起眼,在心裡苦笑。或許我們能夠以智慧超越生死,但愛情可能才是人生中最難參透的事物。
可是我好像只是原地摔倒似的,又掉回到小書齋與阿芙羅黛蒂旁邊。
「據說你在童年曾經考慮過自殺,所以我有預感你會選擇實踐它而徹底放棄身為一名存在主義信徒的理念與堅持。雖然我很想同情你,但是自暴自棄、放棄生命的人從來就不值得被拯救,何況你還是生命哲學的認同者,更不應該拿神聖的死亡來當成你懦弱與逃避現實的藉口。不過,現在的你倒是有機會可以稍微體驗一下西西弗斯跟普羅米修斯受苦時在想些什麼。凡人尋死以後還能活下來的奇蹟可不多見,你要不要再試一次呢?怎麼樣?」
我這下子明白她不會讓我去死了,若我繼續那麼做只是在浪費時間。她要我在現實中活下去,逼迫我否定過去迷失的自己,在未來的世界裡繼續生存。
求生不能,求死又不得,是常人在這世間最大的不幸,也是人類的宿命。日復一日的生存就是禁錮我們的牢籠,充斥於日常生活中的煩神、憂愁與壓力則是體現了存在者的生存狀態。然而選擇死亡與呆滯來逃避現實之苦,既無法給予也無法創造未來,卻只是繁衍更多的死亡與不幸。
這也就是說,學姊與我在當時已經親手熄滅了相愛與共的火苗,老早就殺死了彼此共有的未來命運。我之所以變得肥胖而她漸形枯萎,都是因為彼此壓抑自己又互相傷害的緣故,因為我們都是太過於體貼對方的性格,重重壓抑了自身的生存意志。
為什麼我們不能共同想像擁有彼此的未來?卻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成全對方呢?不對……真相是我們否定了自己對彼此懷有的愛情,卻為了保全對方而拒絕對方存在於自己的未來裡。我們懷疑自己,不相信自己會得到幸福,拒絕冒險,而生命就是一場最崇高而神聖的冒險。
不知怎麼,一股恨意、怒氣與悲働從此自我胸中竄起,深鎖著我的眉頭,身體也逐漸發燙。被遮蔽已久的一股自我存在感開始蛻去蔽障,逐漸變得澄明。
海德格曾在寫給漢娜.鄂蘭的情書中引述過聖奧古斯丁 (Augustinus Hipponensis) 所作的一句拉丁詩文:"Amo: volo ut sis." 中文譯為「我愛,我要你存在」2。漢娜.鄂蘭終其一生都實踐了這個觀念,成為海德格在二戰後餘生中的最大助力。我個人以為,這句話或許可說是存在主義哲學對於愛情的最佳註解。
愛情的本質是渴望存有,若選擇貶低自己去成全對方,就是違反存有的最大謬誤。每個情人都必須重視自己,成就最美好、最強大的自己,成為對方所愛與唯一的愛。
即使世界拋棄、否定我,我也要去愛這個世界。這樣做,在世界之中的那個人就能永遠與我的愛同在,我也能夠存在於對方所身處的這個有我付出愛的世界,不再害怕與失望,勇敢去闖。
所以我們更應當去愛那個曾經傷害自己的人,這個世界才會多一分愛,而不是否定自己付出的愛,更去傷害這個已被減少一分愛的不幸世界。
在此刻重新審視眼下事物的價值後,渴望生存的欲望從我的心底如泉水般湧現,也許這正是權力意志的真正面目。
我終於瞭解,這一切苦難都是源於我們的自私。我們太過於渴望擁有對方,企圖吸走對方的生命,填補自身的寂寞與空虛。當我們警覺到自己的缺陷與錯誤,卻已經在彼此的生命中鑿出更大更深的黑洞,推對方陷入而難以逃離。
「是的,你當時就應該要憤怒了,先面對你應有的情緒吧。」阿芙羅黛蒂說完,向後退了一步。
我拾起一只小屋旁的瓦盆,看著裡面她曾親手栽種的帶刺多肉植物,彷彿看見卑微受困的自己。在淚水浸染的視線中,我憤怒底將它擲向小屋的玻璃窗。
「乓啷」一聲,玻璃碎了滿地。我哭嚎著,聲淚俱下,跌坐在地,在逐漸天明的夜色中看著窗戶上殘存的玻璃裡倒映的自己在受苦受難。
此時一股存在的感覺向我靠近,接著有隻手伸來我眼前,作勢讓我能扶好站起。我一眼就認出那串熟悉的琉璃念珠,它正戴在自己所攙著的這隻纖細手腕上,窗上玻璃殘片正倒映著她的長髮與側臉,瘦骨嶙峋的身形令人不忍卒睹。
心想這是化身為那個人的阿芙羅黛蒂給我的殘酷試煉,我益發憤怒,硬起心腸睜大雙眼,堅持視線面向小書齋。我甩開那隻手,決定不再讓她阻礙我。
一旦拿出了態度,人類就已經做了選擇。
我大聲怒吼,泣叫,咳嗽不止,嘔吐連連,情緒既悲傷又憤怒,發現自己倒映在窗上玻璃殘片中的臉孔與身體逐漸發生變化,整個人在每分每秒變得更加消瘦、憔悴,幾乎退回當年的模樣。
「很好的開始」,女神的聲音似近若遠,接著說:「既然你已經掀開了自己的偽裝,就繼續面對你應當接受的現實吧。」
我開始在她身邊大展拳腳,接二連三擲出盆栽。瓦片與石磚或破或碎,青翠園圃從此亂成一團,小屋牆邊盡是翻倒的植物與泥土,皆是我以狂暴之姿讓眼前文明世界重新裂解的原始秩序。
原先根據我意識重建的小屋門窗全都已被我毀得殘破不堪,此刻成為女神為我特別設置的試煉場。我已不想再看見關於小書齋的一切,於是靠在牆邊站穩腳跟,伸出雙手奮力推牆,以全身所有的力量不停擠壓、衝撞,或許就像西西弗斯推著巨石的模樣。我感到自己手上雖然仍在動作,思緒卻逐漸冷靜下來。
「謝謝…妳為我所做的一切……」我邊動作邊對著小屋喃喃自語。其實我早已感受到她的情意,我早就該這麼告訴她。
即使臉上的淚水已因為熾熱的怒氣而蒸發殆盡,痛苦與悲傷的感受卻仍充滿我的身體與心靈。我回頭繼續赤手空拳底猛打、敲擊眼前的堅實泥牆,只憑紅腫的雙手企圖破壞與消滅這個禁錮自己精神的凝滯宇宙。
「對不起……」因為我不懂得回報,不曾為感情付出,不知如何去愛一個人。
當我接受自己不能去愛她,也就接受了自己所虛構且信以為真的生存目標與價值,從此造就了生命的扭曲,甚至導致我為了虛偽的見證物而寧願選擇毀滅自我。但是我從此刻開始逆轉回來,正視自己生存的事實,承認自己愛過她,尋求回歸生命旅程的正軌。
「請妳…原諒我……」錯過了彼此,交叉的兩條向量直線惟有漸行愈遠,無法回頭。
如果有天告白時被對方發卡拒絕了,你不該欺騙自己「反正我也不怎麼愛他」,你應該微笑底說「我還是會永遠喜歡你」。
因為那個人曾經映入你的眼簾,他的一舉一動都得到你不假思索的注視與關切,他的一言一語也令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愉悅與安慰。當那個人存在於你的人生風景中,他就已永遠是你生命歷程的一部份。無論你在未來是否過著幸福的生活,那個人仍在你心中永伴長存。
那怕是一點點喜歡,也是小小的愛苗,何況是相知相惜、互有情意的兩個人呢?承認彼此之間的愛情,即使它如朝露般轉瞬消逝,都會使每個人更堅強,更加茁壯。
「我愛妳──!」
我不假思索使出所有力氣大吼回應。這是我最想說的一句話,多麼盼望她此刻能聽到。
「笨蛋…...」
深埋在記憶裡的熟悉聲音傳入我耳裡。
可我腦海裡卻接著浮現一片空白,身體愣住,動作隨之停下。霎時間,眼前牆壁開始龜裂,腳下地板漸次鬆動,小屋緩緩往前傾倒。整座公寓建築響起巨大悲鳴,梁柱爆出鋼筋,揚起陣陣塵土,樓板朝下墜落,即將崩塌成斷垣殘壁。眼看自己就要跟著捲入,摔向地底。
潘朵拉的盒子被徹底毀滅,將它深鎖囚禁的東西還給這個世界。
在即將失足下跌的一瞬間,我回首望向阿芙羅黛蒂。漂浮在半空的女神正對著我微笑,並且雙手摟住一位發出溫暖光芒的長髮人影。只是我還來不及看清楚那人的臉,四周就突然變成了溫暖光亮的地下室餐廳,又重複一次跌倒在原地的疼痛感。
「你總算回來啦!」阿特羅玻斯看著一臉茫然的我,捏捏我那已然消腫的清瘦臉蛋將我喚醒。
我的腦袋還在疑惑,試圖理解剛剛那是什麼情況?我是不是見到了誰?那是夢嗎?怎麼會如此真實?紅腫雙手滿是傷痕,而且我的外貌還似乎跟著改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我的任務就算完成啦。感謝二位協助,合作愉快!老娘我還得繼續趕場,掰掰!小帥哥!」超開心的她又捏了我一把,馬上轉身一躍,像廉價的電視特效般颯爽底消失,連餐廳大門都不想經過,我都還沒機會請教她的工作內容呢。對了,她剛講的小帥哥是指誰?
「你還好吧?需要我為你做點什麼嗎?」厄洛斯關心著剛被吃兩口豆腐的我。但他似乎對我外貌的變化不怎麼驚訝,我猜測他應該知道我是怎麼被他媽媽調教成這副模樣。欸…這該不會是他們團隊的 SOP 吧?
「嗯,我有很多疑問,但其中有一個最為重要,請你務必要回答。」語畢時深吸了口氣,我還沒適應這種消風的感覺,不單是因為襯衫、長褲都變寬鬆,讓我像是演出黑白喜劇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 的 Charles Chaplin,主要是還有尚未廓清的重重黑幕與陰謀。
「你問吧,我盡量幫。」他拋開疲憊,慵懶姿態突然變得警醒而且有精神。
「你們是聽到誰的祈禱來對付我?是我認識的人嗎?」
「我不認識對方。按照規定,我們不能透露禱告者身分與委託內容,而且也沒有這種必要。事件往往會很快得到解決,不留痕跡。除非我們失手被人識破。」
他明明說過對方是個「棘手的委託人」,阿特羅玻斯也用「棘手」兩個字來形容自己的工作,況且阿芙蘿黛蒂也說這位委託人也許應該去求助於赫拉而不是他們,這是為什麼?假設他們講的是同一位祈禱者,那一定是我認識的人,而且可能直接或間接跟學姊有關。
「喔…是這樣啊。」換我看向摩耳甫斯,他假裝照鏡子梳頭髮沒在聽我講話。
「摩耳甫斯,你先帶令尊回去休息吧,這邊由我來收拾。」厄洛斯說道。
我心想這莫非是職場上完封對手的止血密技,太高明了。只能怪自己何必轉頭去看摩耳甫斯,導致唯一的籌碼被莊家收走呢?
「喔好,謝謝啦,麻煩你善後囉,嘿嘿。這位大哥,以後有緣再見啦,沒事別夢到我唷,呵呵。」他實在很機靈又話術高強,找到機會就能溜跑,難怪善於偽裝去當史拜,非得要實力派角色才能制住他。
由於現場時空秩序與睡眠狀態直到摩耳甫斯帶他父親離開才解除並回復,現在餐廳除了其他顧客,剛剛一起出發辦事的成員只剩我跟厄洛斯。我們相對坐在同一張餐桌前,各自喝著咖啡休息,閒聊幾句。
我們不打不相識,像熟人似底聊開來,意外找到一些有趣的交集與雷同,好比說他跟我都算是擁女主義者 (pro-feminist)。我對他們集團抱有許多疑惑與好奇,他也盡力在權限內為我釋疑。雖然有不少機密細節無法對外人直述,言談之間仍然讓我確認了一些有關「M 女士」的資訊。
「和你聊天很愉快,我也差不多得去處理其他委託了,今天就聊到這邊吧。……你已經不是以前那個你了,對嗎?」厄洛斯再次確認我不是僅有外貌改變,大概是為了回去向他母親覆命交差。
「嗯,不是了,應該不是。」我搔搔頭。
「應該不是也必須不是。」他笑著模仿一遍我的臺詞,鬆懈下來恢復原先那副溫文有禮的青年模樣。但是他渾身不停散發男女通殺的超級魅力,美男妖精氣息滿到破表,跟他同桌讓我有點吃不消。
他大概發覺我神情有點彆扭,笑著提醒我:「眼見不一定為憑。我們往往只能看到心中的想像,而不是事實真相。」又建議我說:「你應該對自己更坦率一些,才不會讓壓抑的情感又傷到自己。」他說得誠摯,我謝謝他,不禁稱讚他的率真與熱情,擁有無與倫比的大愛。最後他站起來準備動身,提議我們互相握個手,算是和解。
「我也許還會再見到你,你的命運已經變了。」他說。
我點頭苦笑,心裡好奇為什麼一個已婚大叔還會再次遇到愛慾之神?這真是個謎團。
「後會有期,再見。」
我站著目送他從餐廳出入口離開。只是不曉得為什麼他走路又放慢到只剩下四分之一秒速,所以一路上不但有好幾個人盯著他的翹屁股猛瞧,還有人拿手機偷拍,真是個不得了的傢伙。但這恐怕都只是每個人心中的想像,不是厄洛斯的真面目,正如他在古人心目中多半是個胖嘟嘟的金髮小男孩,而且還常常光著屁股沒穿衣服……欸,那我眼裡的阿芙蘿黛蒂為什麼會長得超像志 0 姊姊呢?
雖然厄洛斯沒有說出委託者的名字與身份,但是他在主動伸手跟我和解時眨了下右眼,我手裡接著冒出一張神秘紙條,彼此心照不宣,我猜測這是對我們剛剛那場矛盾大對決的一點小小補償。
我在他離去後回到餐桌前坐好,確認背景音樂、食物香味是否正常,假裝舒展肩頸時左顧右盼,掃視一遍是否還有人在監視自己。
再次檢查感官之後過了幾分鐘,我一手端起咖啡杯假裝啜飲,另隻手小心翼翼底在桌緣底下翻開紙條來讀,卻看到上面只簡單寫了五個字:
" The prayer is your lady."
這個爆炸性內幕讓我不禁暗自尖叫起來,差點噴了半桌子咖啡,難怪他剛才坐在我面前時不想講。
果然是個棘手的委託人,我心想,今天的災難恐怕還沒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