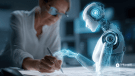學姊給我電話留言的內容是一段地址,要在半夜十二點門禁以前抵達。
我騎車在路上始終無法全神貫注,雖然沒騎快車卻不時想東想西,猜想她為什麼要在這時候見我?是不是她要對我講什麼重要的話呢?
也許她是要告訴我別胡思亂想,因為她其實喜歡同性,那個不帶慾望的親吻只是俠義之舉?
還是她要教我別癡心妄想,要跟我攤牌說她早已有正牌男友,請我們兩人自行找時間決鬥,只有贏家才能當上真正的楊過?(那應該要斷右臂還是左臂呢?)
在我為這些奇思異想找出答案之前,機車已經帶我停在一間公寓門口。她聽見熟悉的引擎聲,知道自己等待著的那個人已經到了,出來開門領他上樓。
學姊在這個學期的住處,是位於學校附近某公寓頂樓加蓋的獨立小雅房裏,像座孤島。
房間外四周圍弄得像渾然天成的園圃,種植了豌豆苗、苜蓿芽等可直接食用的芽菜,還有薄荷、迷迭香等方便提味的香料。在她的照料下,茁壯中的花苗與乾淨土壤時時散發自然清幽的芬芳。
至於室內布置則是書架比衣櫃多、書籍比衣服多,沒有冷氣、冰箱,但有小烤箱、除濕機與空氣清淨機,此外僅有一架掛著蚊帳的乾淨整齊單人床。
依著小屋主人端正質樸的性格,牆上每扇窗各自搭配一塊素雅花色布簾,綴著大大小小散開的葉紋圖案,與粉刷成象牙白的牆壁相映成趣,是一間極簡風書齋房。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為了顧及安全與防盜而不得不加裝的幾何花形鐵窗。它們已然滲出鐵鏽汙漬,僅僅屬於聊備一格。看似默默守護著小屋現在的主人,又像是囚禁著它們的主人。
這是一座靜靜的孤島,就和棲居其間的女神一樣寂寞。
她像個房仲似的介紹說這房東算有良心,沒有將整層樓裝潢得像密集式蛋雞場般來海削外地學生。
我則像是來看屋的承租方,屢屢點頭說那真是很不錯。
我們兩人間的寒暄變得生疏起來,演出像初次登臺似的男女混合雙人相聲,都在掩飾心中的不安。
這股不安從何而來?現在細想,應該是源於兩人關係的曖昧與不確定。
虛構寓言裡的老婦人教給尼采化身的查拉圖斯特拉 (Zarathustra) 一個道理:"Du gehst zu Frauen? Vergiss die Peitsche nicht!" 建議走向(年輕)女人的男人別忘記(帶)鞭子,似乎存心去建立一種意在言外的特殊性關係。
雖然他在上下文有所鋪陳,但我認為尼采並沒有講清楚這條鞭子的用途與去向。根據他愛慕的露.莎樂美 (Lou Andreas-Salomé) 在日後所提供的解釋,這條鞭子或許掌握在女人手上才是正解。更何況就算男人真的緊握鞭子控制住女人,你以為女人就再也無法控制男人了嗎?
此時在我和學姊之間不需要鞭子,彼此身上都只懷著一顆渴望見到對方的心。
房內點亮了幾盞柔和溫暖的裝飾燈,學姊領我走在地毯上圍著如小山般的書架堆裏,就著和室桌前榻席坐下。我有預感要在彼此距離不到三十公分的空間裡交談,看著對方的臉孔,直視對方的眼睛,回復到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交流方式。
語言在此時彷彿是多餘的,又好像應該是彼此傾吐的。我們陷入很長一段時間的沉澱,也許,似乎,大概,可能,應該,說不定有一千年那麼久。彼此不曉得在等待什麼暗號,又好似在期待什麼變化,或許都在等對方先出手拯救自己。
我們很有默契底用沉默來省略對彼此都虛偽的開場白,但氣氛依舊尷尬,而且不知該作何表情,眼神也毫無交集。最後,她意識到自己身為女主人的義務,先開口說話。
她主動告訴我這兩年空白的經歷。先是在高中階段患上憂鬱症,進大學後時不時發作,拖到大二又開始出現症狀才被迫休學。她經過安靜調養一陣子後好轉不少,於是重新找份時薪工作學習回歸社會,再拿所有攢下來的積蓄飛去法國巴黎近郊讀了幾個月語言課程。返國前,她先寄了一整箱從古書店蒐集到的精美插畫本和二手文史哲學書回家,一進門就提醒自己還有精彩人生等著要過。
她說自己想做一名學者,以後研究古籍版本,或是去當古書店老闆娘,問我將來有何打算。我說自己未來想去德國讀書,如果拿不到獎學金就去讀神學院,回來做神父。她咯咯笑著說我這人真是個自以為是的浪漫笨蛋,人笨又沒結婚就太可憐了,還說我應該要先學好拉丁文改去義大利才是正解。
她笑得很真實,很純粹,也很美,我眼裡的她早就不管說什麼都是對的。
此刻的她並不像平常在課堂見到的仙女模樣,也不全然是陪 Kuro 玩耍的狗媽媽,而是一個真真切切的人類。也許是現實世界的魔咒被解除了,不必再裝扮成精靈、仙子或俠客的女人回歸自我的本然原貌,重新成為一個單純的小孩。
看她心情頗佳,既然想多了解她,我就順勢開口問了:「妳是怎麼開始生病的?」
她抿嘴收斂笑容,輕輕轉低頭把眼神移開,反問我:「你沒有聽說過嗎?」
在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許多特寫畫面在我腦裡快轉。她拿著平時戴在左手腕的那串琉璃念珠誦念經文,還有從百貨公司專櫃特地買來的嬰兒鞋,因為 Kuro 媽媽不幸喪生而流不停的淚水……事情的真相、細節雖然未必能夠盡知,其實早已溶進我們生活的殘酷現實裡,謠傳的虛構內容往往混雜著幾分真實。但何苦要屢屢追究,有意無意底逼使他人撕開好不容易癒合的瘡疤呢?
同時我發現自己又犯了類似下午上課時的錯誤。這次不僅在不該問的場合問錯問題破壞氣氛,而且我了解到自己其實也在窺視著她,並沒有比其他人高尚多少,甚至虛偽底可憎。滿心盡是憐憫與歉意,我感到深切困窘,臉頰燙得火熱。
「哎呀,事情過去就不提了。」她察覺到我心境的微妙變化,切換語氣換話題給我安排一個臺階走下來。
「所以你現在懂得什麼是妖精打架了嗎?笨蛋學弟。」她在語言裡藏著體貼。
「大概懂一點了,但不曉得這說法從哪邊來?還請學姊不吝指教。」一邊假裝搔頭緩和情緒,我真是笨得演技低劣。
她得意底起身,伸手從一排與視線同高而且排列得特別整齊的書架上抽出幾種《紅樓夢》版本,指示我翻到第七十三回自個兒去找。旋即湊過來問我要不要聽她今晚剛買的音樂專輯。
我點點頭,於是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渾厚嗓音開始輪流在她房間裡輕輕揚起。歌曲一支接一支傳唱,每個句子、每個音符排隊從音響喇叭小小聲流洩而出,散佈在室內每個角落。
她又動手沖好一壺咖啡,用產自印尼蘇門答臘的深焙咖啡豆香裝飾空氣,對這難得的午夜聚會再適合不過。知道她把我放在心上,我深受感動。
「請你嚐嚐看。」
她像個小天使似的遞給我一只杯口塗著金漆、杯身繪有蘭花的高級骨瓷杯。濃烈溫潤的熱氣不斷飄逸四散,早已薰得整間房都是咖啡香味兒。待我淺淺飲了一口,她不等我出聲稱讚炭烤深焙的甘醇之美,卻突然伸出她那雙冰涼玉手扯住我的火燙臉頰輕輕向兩側推拉,看著我的眼睛認真說道:
「學長,你今晚可不能倒在這裡睡著,萬一我們真的像妖精一樣打起架來,彼此會恨對方一輩子。」
「我~也~這~麼~覺~得~~但~是~妳~可~別~比~我~先~睡~著~喔~~學~妹~」我雙頰受迫,只能用類似鴨子拉長音般的奇怪腔調回答她。
「很~~好。」她很滿意這個答案,模仿我那奇怪語調講話,把我的臉頰向內輕壓送還回來,彼此帶著羞澀的表情相互微笑。
於是我們就在她棲居的這間仙女小書齋裏邊品嘗咖啡邊聽音樂,談電影,聊著關於人生中林林總總的大哉問。光陰稍縱即逝,時間緊迫,我們不能分心,不可以停下來。我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裡討論存有,在一小片世界之中認識時間的本質為何,享受生而為人的幸福,還有在茫茫人海中遇見知音的莫名幸運和莫大喜悅。
時間一分一秒來臨了又過去,直到天色漸明,她趁左鄰右舍尚在半夢半醒之際領我悄悄下樓。待我伸手準備摸黑打開公寓大門,她從我身後擁抱過來。
「抱歉奪走你的初吻,沒想到你竟然是這麼純情的人。」
在一片黑暗的樓梯間裡,彼此的距離再次縮短到三公分以內。
「謝謝妳幫我解圍,反正我也沒吃虧。」我偏著頭靠向她應答。
「原來你如此居心不良,敢扮豬吃老虎,以後去當神父恐怕會被勒令還俗唷。」
「我倒覺得母老虎的脾氣該收斂一點,否則去大學教書當掉太多人會被投訴哩。」
「不可能,美女無論做什麼事都是對的。」
「說的也是,那我就勉為其難承認妳的確是美女。」我真的沒說謊。
「大笨蛋。」她用力捏了一把我蓄勢待發的鮪魚肚。
「那這場就算我贏了。」有點疼。其實正中柔軟腹部是很疼,但我得忍住。
她沉默了一下,我感覺到些許微妙變化。
「我恨你…為什麼直到現在才出現在我眼前?…為什麼…你會在我的生命裡遲到?」她開始邊說話邊啜泣著。
我閉眼皺眉,無法回答。
「你不准去當神父,答應我…你得結婚,生一打男孩組成球隊踢下世界冠軍……你還要當上教授代替我去誤人子弟,寫很多很多書,當掉很多很多學生……我羨慕最後會成為你妻子的那個人,為什麼我無法像她一樣愛上你…我好忌妒她……」她情緒激動著,像個失去依靠的孩子。
「對不起……」她突然又安靜下來。
我恐怕不能接受這句道歉,也許我真的罪有應得。
「妳開始胡言亂語了,快去睡吧。」
她仍沉默著,雙手圍得更緊。
我閉起眼一心感受她的氣息與暖意,將手心的溫熱換取她雙手的冰冷,內心質疑為何我們無法彼此相愛。
如果我對她有感情,為什麼我卻沒有動作?為什麼我不承認她在我心裡有個獨一無二的位置?為什麼我不能愛她?為何我要接受她的獨斷決定?我在遲疑什麼?或者說,我在懼怕什麼?
「我不能…讓你…的人生中…遲…苦…一輩子……」她的話語夾在哭泣聲中,時而微弱,幾不成句,我甚至聽不清楚其中幾個字。
「妳在說什麼傻話?...即使晚來了,但我不是已經在站在妳眼前了嗎?」我希望她能聽進去,卻感覺到她漸漸鬆開了手。
等我下定決心轉身要親吻她的時候,她彷彿預知似底從另一邊閃掉我不流暢的彆扭動作,搶一步打開公寓大門走出戶外。
「又是新的一天…清晨的空氣最乾淨了,不是嗎?」
她背對我,一如以往平靜底說話。從幽暗的樓梯間朝門外看去,她彷彿整個人被圍繞在紺碧色拂曉的冷冽空氣中。
「是啊…那…我先回去了。」
一去不返的機會織成了牽動命運的細索,我只能在眼底留住她此刻的背影。
「晚安,明天見!」
「嗯,晚安。」
我們就此在清晨空氣中快步分手,沒有加演依依不捨的十八相送,也沒有直視對方眼睛互相道別,只怕看一眼就禁不住辜負彼此之間的承諾與無暇純潔。
不比夜空裏的星辰般緊緊靠近彼此,學姊與我之間的短短緣份就如朝露雲靄般底逐漸逝去。她的真實存在、她的溫柔體貼讓我了解到這個可憎可厭的世界仍有其溫暖可愛的一面。
古諺有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人生海海,必定經常遇上困頓與低潮,但你不能不為遲來的順風遠揚預做準備,過分底妄自非薄而看錯自己在未來的份量。誰不曾在夜裡獨自枯坐,懷抱身上所有寂寞入眠?你可知道炸裂出兆億光熱的恆星無法映照自己的內心,闇黑無際的冰冷宇宙則包容一切智慧與無知,快樂與悲傷,還有幸福與不幸。虛以存實,實中藏虛,世間所有事物唯有善惡兼容才能得到和諧圓滿,還有超越生死的永恆。
學姊與我此後見面、對話依舊和過去毫無二致,彷彿那天所有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但是昔日的漫天謠言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系上再沒有人在背後對她指指點點,也沒有人膽敢在我們面前像青春期沒結束的小毛頭那般亂開玩笑。
我彷彿突然開了天眼似的,包括系主任在內把關的多數學期成績不但歐趴還名列前茅,而學姊也收斂脾氣從此不在課堂上自由開嗆,總算是開低走高順利拿完必修學分。但是高年級的選修課讓我們愈來愈少在學校見到彼此,她沒再給我電話語音留言,我也不曾再去過仙女小書齋。
因為我們已掃除此刻的人生迷惑,知道必須活得健康進取,這樣才對得起在那宿夜晚與自己分享生命的那個人。
始料未及的是,男孩即將慢慢開始變形得像是心寬體胖又眼皮下拉的可愛怪獸,女人則將漸漸枯萎得像是西伯利亞冰原上的冷凍乾燥花。這些點點滴滴的改變預告了我們未來事與願違的人生際遇,也間接形成了我對亡者墳塚的深刻恐懼。
由於每學期研修學分數上限與主修學程的開課規定,我最後仍不得不為六個學分的一門學年課多留校一年,結果變成跟學姊同時畢業,但是我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見面,彼此間的交集只剩 下Kuro。
學姊的待修課仍比我多,雖然不清楚她的具體情況如何,但我每周只去學校一天,其餘時間輪流在咖啡店、圖書館與連鎖書店打轉,接在學姊給我的啟蒙之後,繼續獨自鑽研一些看來不怎麼有錢途的學問。
我們像分居的夫妻似的很少去看顧孩子,幸好有新來的學弟妹陸續加入照顧 Kuro 的行列,我很高興牠有新的家人陪伴。據他們說,一位看起來如仙女般氣質的美麗學姊跑遍了校內各系大一班,介紹包括 Kuro 在內許多棲居在校園的動物,宣導正確的動物保護概念,希望有人能組成團體一代接一代去照顧牠們。
我聽了很欣慰,這的確像是她的作風,也真的收到效果。相形之下,她想得多、想得遠,而且實際可行,我卻仍是個空轉理論而且過份浪漫的笨蛋。
重新回憶辦理離校手續的那天,正當梅雨季結束的濕熱初夏,助教大姐要我領到畢業證書後一定要回系辦一趟。她交給我一只某人託她轉交的小小正方型禮盒,我打開來瞧,是一條具有成熟韻味的雅緻領帶,底下壓了一小張以秀麗行書印著「鵬程萬里 don't be silly」無俚頭祝福語的未署名空白小卡。
助教大姐說這條領帶沉穩莊重,適合社交場面,戴起來就會像系主任出席研討會或學界年會那般盛裝登場。我很難想像自己穿成老前輩那樣去參加會議,但是大姐說,選這禮物的人用心甚深,希望收到的人有朝一日能夠擁有適合配戴它的身分。我們心照不宣,都明白那兩人是誰。我向她道謝,她祝福我們都能擁有幸福美好的未來。
我也去向 Kuro 道別,讓這齣家家酒似的虛擬家庭有個結局。
學務處在不久前順從民意,推舟行水,讓學生成立動保社團。於是學生會福利部門著手動員組織,開始統計造冊散居於校內各處的幼仔貓、老病狗、游得慢的雁鴨、爬超快的烏龜、常被老饕釣客騷擾的錦鯉、鱖魚還有隨季節才會出現的各種候鳥,甚至遍及各系所辦公室偷偷飼養的搞笑八哥、假迷你兔跟寶貝天竺鼠。
他們在學校網站主頁上特別設計一個區塊來經營,每日輪播各種校寵與系寵們的近期照片,讓畢業校友能隨時上線訪問,開放留言聯絡彼此感情。這番事業現在能夠做得那般有聲有色,源自學姊倡議鼓吹,奔走革命,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應當記上一筆。
Kuro 此時快滿三歲,活潑好動,而且追逐蝴蝶時跳得愈來愈高,速度也跑得飛快,溫室早已裝不下牠對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學弟妹已準備在暑假幫牠搬家到學校圖書館附近,牠將成為第一隻進館吹冷氣伴讀的校寵。
見到牠特別令我感傷,牠就像是我與學姊共同養大的孩子,但現在卻是我們這對養父母得離巢的時刻。
我再次幫牠盛滿乾淨清水,看著牠的眼睛摸摸牠,給牠記住我的氣味,最後跟牠道了聲再見,就像學姊可能會為牠做的那樣。我們將從此天涯兩隔,願牠接下來的日子依舊過得開心,在這塵世間就能離苦得樂。
《莊子.大宗師》載云:「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就像那故事裡的小王子再也沒有回到玫瑰身邊,卻永遠留在狐狸的心裡。大底凡人未曾經歷痛苦,怎得體會歡愉?又怎麼會靠近彼此、認識彼此?你我像是其中的誰?希望成為誰?又渴求著誰?是否願意永遠惦記著誰?
雖然男孩在那晚沒有帶鞭子去女人身邊,但是女人在離開男孩之後留給他一條領帶。我知道這不是枷鎖,自然也不是束縛,但我始終無法定義它是怎樣的存在。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或許你們能告訴我答案吧。
自從學姊在那夜播放了我當時最喜歡的音樂專輯後,其中有段旋律從此在我腦海常駐,偶爾自動自發底點播起來。此刻,永遠的高音C之王又開始在我心裡唱起這首歌曲:
Nessun dorma! Nessun dorma!
Tu pure, o Principessa,
nella tua fredda stanza,
guardi le stelle
che tremano d'amore, e di speranza!
Ma il mio mistero è chiuso in m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