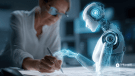時間不早了,但我得等室友「M 女士」回來,在離開地下室餐廳前必須儘早跟「她/她們」好好談一談。
背出門的那堆書早就翻完了,手邊也沒有筆電、手機,此刻還能如何?只能利用所剩不多時間繼續隨便擠點東西充進度。有經驗的前輩都這麼說:缺乏靈感也無妨,壓力才是趕稿時的好朋友。練習去硬刻出字字句句塞滿整張稿紙,先寫出來再逐字逐句修改,總比幻想一氣呵成有效率得多。
幸好,平時紙筆總不離身的習慣拯救了坐困地下蟻穴的自己。
想想今天經歷過那麼多怪事,除了讓我尋得一些昔日記憶,也領回一部份曾經學過的知識,但這幾齣實境冒險秀讓我到現在還有點膽颤。
深呼吸,再深呼吸,我得讓思緒平穩底落下、反芻,埋葬阻隔它的情感於飄渺無盡的時空裡。其實,要不多虧了那幾位莫名其妙跑出來的古代神祇,我還不知道囤積在身上無處宣洩的情緒就是自己身材嚴重走樣的原因,可是經過剛才那段詭異又神奇的醫美過程之後,我現在的外貌變得不大一樣,不曉得至親好友是否還會認得我?該怎麼交待這個變化?如果和盤托出真相與細節,她/他們真的會相信我接觸到無可名狀的神祕力量嗎?
不但得要有個說法才行,而且還要考慮事件委託人——我老婆,簡稱為夫人或敬稱為女王——在其中的角色,這就夠令人煩悶了。
有件事是確定的:廢話、喃喃自語是一切故事的源頭。不過你得知道我講這些字眼都沒有負面含意,它們類似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第一樂章的首段音符,是開啟神秘匣子的聲音。有了它們,我們的注意力才能集中往那個方向去凝聚,去傾聽世界道出的呢喃,讓我們的意識去解讀它揭示的種種訊息。
將意識化為文字符號的過程,無論是福至心靈底落筆,抑或言不由衷底儁刻,理當是我再正常不過的日常生活,偏偏它受到重重阻礙,因為我讓自己產生腦霧去阻擋記憶,連帶影響了意識的正常流動。這樣我也就理解自己為何有時需要邊聽音樂邊讀書,還有為何偶爾出現耳蟲:反覆播放的音樂讓我可以察覺時間的流動,繼而開始進行工作。
今天漫長底不可思議,如果可以,真想在嘴邊咬點什麼東西,或許多少能轉移此刻再度浮現的焦慮。交替浮現的夢境、記憶與昔日親歷的命運事實場景意外塞進這個應當老實工作的大白日,那些連番播映的內容情節已占據腦海,難能揮去。它們既古老又龐雜,蒙太奇般底倒置,無來由似底錯亂,彷彿一會兒上映校園青春劇,一下子又跳到跨時空史詩。這有點像是被迫連趕兩三齣早、午場電影的倖存感,順著光影擠壓出的疲憊還輾上早先的憂鬱,而且接下來我還得要根據那些內容去找某人對談,追查隱藏在事件背後的真相,想到這邊又覺得更累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愈給出答案,卻又冒出更多疑惑。我真的親歷過剛才的情況嗎?那難道不是內心的想像嗎?感官的閉塞、身體的變化,以及渾身沉沉的疲憊感,為什麼不能證明我曾經親臨那些神秘時空呢?雖然它們荒謬底更勝荒謬的故事,若我放下不可置信的態度去接受它們,那些故事對我這個人不就是真實的事物嗎?而且我並未瘋狂。
我想自己是透過古代遺留迄今的某種神秘力量,回到了我曾親歷的昔日場景。它藉由留存在自我意識中的感受來重新塑造,換個比喻講,就類似一個打造得精妙絕倫的攝影棚,而且連我本人都沒有感受到差異,相信自己回到了過去。英國史學家卡爾 (E.H. Carr) 有一句名言:「歷史是史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而我回到重新塑造的那段過去,補講一句「我愛妳」,又親耳聽到一句「笨蛋」,這算不算是對話呢?
經歷那些被重新喚起的情節後,我接受了昔日不願接受的事實與感情,承認自己對世間事物的嘲諷與不滿其實出於個人私怨與憤懟。這並不容易,不但不怎麼有趣,甚至連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悲哀。或許只有我這麼想:憤世嫉俗是一種自由,一種健康青年才配擁有的特權,否則就會同時寄生幼稚與任性。這就是厄洛斯在發怒時給我的指責。
至於阿特羅玻斯則認為我時常鬼扯、給自己洗腦,去忘卻某些記憶,我想這是因為她未曾了解我的個人狀況而下的判斷。她跟阿芙蘿黛蒂都認為我算是聰明人,這真是個天大的誤會。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 說過:「命運女神不僅自己盲目,而且還使自己所偏愛的人也變得盲目。」她身為命運三女神裡的大姊,曾經帶著兩位妹妹刺殺過一名泰坦神,負責的工作是拿著一把利剪按長度剪斷人類的命運之索,可算是某種程度的死亡使者。理當冷酷無私的她罔顧 M 女士的委託,放任厄洛斯幾近越俎代庖、將毒箭對準凡人的行為,必然違反他們執行業務時的工作規定,這類激烈動作不免有些欠妥。雖然我總覺得那是一場逼我就範的戲碼,但是那群「最接近人類的神祇」其實也經常出包,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亂成一團的神話故事供我們消遣了。
嗯,此刻還有點餘悸猶存的震撼,可是能從他們手裡撿回一命,感覺真不錯,我想自己的命運之線應該還很長。
仔細想想,重歷過去是「M 女士」的主意,並不是我的意思。事實上我逃避昔日發生的往事,努力不去記憶它。厄洛斯他們則是接受我夫人的委託,似乎要把我從阿特羅玻斯手上劫走。雖然他們失敗了,可是在正三角祭壇上,阿特羅玻斯並沒有阻止欲置我於死地的厄洛斯,看來他們兩組人雖然出於不同動機,卻對我有一個共同目標。如果我夠聰明,早就察覺答案了……應該不可能只是單純要折磨我,好讓我減肥吧?
黑幕重重,這世界有太多黑箱……確實,我們的生活裡就藏有許多頗有用處的黑箱,例如相對論、黑洞、時間旅行與哀鳳。
雖然我們不完全了解這些黑不隆冬的盒子裡裝著怎樣的內容物,但你從愛因斯坦、霍金與賈伯斯被暴露在公眾目光的私生活可以得到些許親近的幻覺。因為他們以及其他偉大人物多少面臨過與你我相同的處境,像語文科目不甚拿手、經常生病、不善社交、行為放縱又荒唐,以及樂於成為沒畢業文憑的棄校青年等等。大眾從這些故事知道他們也曾是凡人或比自己更慘的魯蛇,然後在一連串際遇與人生抉擇中才不小心變成了超人,他們在生命中的神奇轉折提供讀者思索各種困頓解方的參照點。
那問題來了:私生活與個人成就的關係是什麼?哪個是雞?那個又是蛋呢?呃…我是說雞蛋。先別考慮是哪個品種的雞,也先不要牽涉到長滿羽毛的恐龍,謝謝各位合作。
不過我必須坦承這是刻意誤導。如果我們同意個案人物的私生活與思想主張、創新成就之間相互影響,雞與雞蛋相生的循環論證就是個假議題。雖然問題可能出在我們無法確知事物發生的具體情況,但也許我們可以從死亡與結束來思考:雞與雞蛋之中是誰第一個被吃掉?
《論語.先進》載語云:「未知生,焉知死?」我們擱置上下文,斷章取義來想一下,這兩句話讀起來似乎對我的建議完全打臉。
不過這句格言在女子十五歲即可經媒合生子、男子二十歲成人、人均壽命在四十歲上下、兒童夭折率偏高、三代同堂並非普遍的時代就出現了。麻煩你陪我精算一下這個可能性不大的理想狀態,看看有無列錯:
甲男二十歲與乙女十五歲成婚,次年生適子丙。
二十年後丙男二十歲。此時其父甲男四十一歲、母乙女三十六歲。為子丙男媒合十五歲丁女成婚,次年生適孫戊男。
又二十年後戊男二十歲。此時其祖甲男六十二歲,祖母乙女五十七歲;其父丙男四十一歲,其母丁女三十六歲。為孫戊男媒合十五歲己女成婚,次年生適曾孫庚男。
列到這邊就夠了。在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實際情況通常更糟,而且範例已達四代同堂——的超理想狀態中,你認為甲男是否能親眼看見嫡孫戊男、適曾孫庚男的誕生?嫡孫戊男與適曾孫庚男能否產生對祖母乙女的個人記憶?(原來我這現代中年大叔若活在兩千年前早就到了可以抱孫子的年齡?!)在那個時代雖然不是完全沒有,但機率應該不會很高,而且很容易出現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情形,例如在晚年喪子的孔老夫子就是如此。「未知生,焉知死?」這兩句話據傳就是出自夫子口中。
長輩為晚輩送終,晚輩卻不見得有足夠的經驗能體察生與死,在青、少年尚未有資格親自培育新生命的時期,更可能早一步去旁觀與經驗他人死亡,變成「未知生,先赴死」的情形。早夭者不得已成為不知冰者為何物的夏蟲,也無法道出死後的感覺與心得,那就完全沒有領悟到「既知死,復知生」的可能性,也就無法體會足以道出「未知生,焉知死?」的心境。
瞭解他人的生命,何其難哉?
以二位元的二進位邏輯運算來看,個位元對應「生」,進位元對應「死」,知為 1,不知為 0。在 00、01、10、11 四組代碼中,生命對於生死的答案是 00 成為 11 的過程,因為我們必須先放空才能填入,在我們生存的當下已經少於一條命了,所以稱為餘生。夫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意謂知生之後方可知死,因此 11 成為這則運算中唯一存在的解。
死亡彰顯生命的可貴與偉大,生命賦予死亡以價值與意義。領會的關鍵在於要存活得夠久,看過誕生也看過死亡,才能相互參透。因為生與死本來就是一體兩面之事,它就像是那條神秘而且神奇的環帶,無始無終。
瞭解自己的生命,又談何容易?
或許就像初戀一樣,事物不知何時開始也忘了怎麼結束。我們不大可能會清楚記得自己出生時的感覺,也未必能仔細感受自己的死亡過程。我們只能透過觀察他人的生死與事物的榮衰來建構屬於自己的想像。人的存在過程就是一場漫長的出生與漫長的死亡,一條準備完成、已然完成最後又被拆解的莫比烏斯帶。
從我們此刻的生活向過去回溯,在商業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尚未促進物質文明更新的階段,上古晚期至中古時代的人類大半在誕生與死亡交錯的世界中無助底尋找出口。假設居住在上古的東亞世界,一旦身體出了毛病,還得在官、私社求神問卜之餘,千辛萬苦找著巫醫、方士消災解難,萬分感激底拿著狗屎狗糞製成的萬用藥丸——內用外服兩相宜——可能還搭配無法確定是否為真貨的童子尿一同使用。後來在西方肆虐數世紀的屢次黑死病,仍對人類生活造成重大威脅。此後的時代雖然物質文明進步許多,但終究不比今日所生活的世界來得便利與氾濫。
每每看到穿越劇中男女主角詩情畫意的生活情調,個個不是王公貝勒就是貴妃格格,只需煩惱愛戀,無須擔心吃穿,確實好不愜意。雖然我也曾心神嚮往,但我再怎麼渴望也不要穿越去沒有咖啡館、衛生紙、含碘鹽、乾淨飲水、彈簧床墊加溫暖被褥與網路電商的時代,連回到較晚近的一百年前都不是很願意。大部分人類再怎麼免疫力超群也不可能一輩子都是身強體健呷百二的藍波(John Rambo)。
對了,我差點忘記還有民主制度、垃圾分類與汙水處理設施、全民健保體系、洗衣機以及便宜又乾淨的能源,這些一個都不能少。你是否覺得這聽起來像是癡心妄想?其實我也這麼覺得。
例如上述的最後一項,能源的製造、轉換與輸送必然有所污染、耗損與浪費,並且與生產規模成正比。所以你是選便宜的,還是乾淨的能源呢?總不可能選昂貴又不乾淨的這一種吧?那為什麼我們居住的環境裡總是舉頭三尺有空汙呢?當我們每呼吸一口氣都是在找死,又是什麼原因讓我們努力要生存下去?欲望?情愛?生存意志?不管是為了什麼動機與原因,那只有在自己身上才能成立,形形色色的生存邏輯簡直荒謬得真實無比而且真實底無比荒謬。
那我在此順便友善提醒各位有實力與熱情來回穿越古代的讀者朋友,多多享受那個時代的乾淨空氣,出發前千萬別忘了攜帶個人藥品、備用眼鏡、球鞋、巧克力與十八歲以上才能購買的東西,這會讓你在物質不充沛的環境下過得比較輕鬆。對了,想要穿越回到工業革命後的近代大都市之前請記得攜帶口罩,那邊通常有嚴重霾害。
對於喜愛上古與中古時代的朋友,即使你動作敏捷、體力驚人,很有希望在較量生死的武鬥場合中脫穎而出,我個人還是建議你最好要先練過一下花體字跟毛筆字,因為你十之八九不大可能精通古典及通用希臘語、拉丁語和中古漢語,但至少能讀能寫是你在那識字率不高的時代的獨特優勢,穿越過去至少還可以假裝啞巴當個文抄工混口飯吃。(如果有人表示他隨時可以回到現代補給,那就當我沒說。)
可是如果在那個地方能保證找到每個人生命中的真愛,你要不要穿越過去呢?這倒是個值得大家一起探討的真心話大冒險。
不過我有些疑惑,再請你幫忙想想:人類社會在原始蠻荒與文明開化的對比下,如果沒有進入一個比起此時此刻更好的世界或具有可能性來實現美好生活的環境,為什麼我們要選擇它?為什麼總有人覺得過去是個美好年代?我們是否可以利用現代知識回到過去當大王?企圖直接跳躍到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是否不智?這是否因為我們對於未來遠比對過去一無所知而且不抱希望呢?如果有真愛在身邊陪同,你會改變自己原先的選擇嗎?
這些問題的假設前提是基於人性的利己傾向與利他行為。時諺云:「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又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據說這個世上很少人具有甘願犧牲自我以成就他人的高尚情操,但是在我的親身體會裡,以母親為主的一等親身分毫無疑問是這類人物的典範、表率。因此我個人為了時時不忘彰顯她們的傲人成就:生養我與飼養我,我常(ㄅㄧˋ)常(ㄒㄩ)自(ㄉㄟˇ)動(ㄧㄠˋ)幫母親大人與夫人洗碗、做家事、跑腿與負責講笑話,扮演類似厄洛斯那樣的乖寶寶。那你咧?嗯,我好像又岔題了。
咳…所以囉,你不覺得問題出在我們那已然貧瘠的想像力嗎?誰教現實中的便利生活與智慧型工具儼然深深底困住了我們的思考。無論你點頭、搖頭或猶豫,我都當你是同意的意思,那要不要學學億萬富翁在洗碗的過程中找到人生最美妙的快樂呢?人生不僅不能窮到只剩下錢,也不能富到只有錢,知識、權力也一樣。你有想過自己最富有的東西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唯一不接受的答案就是貧窮,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也必須有值得自己驕傲的東西,那怕是一粒承載整個宇宙重量的沙塵,一段永遠消逝的感情,那也是一種驕傲。
又例如說,你是否抱怨過那個令你生活一團亂、占用大半時間、經常使喚並遙控你打雜的情人、親人、家人與活像個天外來客的小小複製人、前世情人?他們實在很不可愛到令自己既生氣又苦惱。你總會希望他們別吵你工作與睡覺,最好他們都乖乖閉嘴、收拾滿地玩具並洗好衣物自動晾乾,不須自己動口動手動腳就能完成所有份內事,甚至餵你吃飯喝茶也別噓寒問暖,更別關切你的肝是否太操勞、手上工作進度到哪邊、何時有空陪陪他們。
但其實要不是他們整天吵你、干擾你做事,像隻寵物或小嬰兒似的要你陪吃陪睡陪笑陪聊天,恐怕你不見得會想辦法讓自己努力走在生活的正軌上,也不見得能產出、上繳早就該達標的業績份額與勞動果實。是的,你我好比是自高加索山頂被拯救之後的普羅米修斯,雖然肝還留在身上,那副連著一小塊山頂岩石的腳鐐已是身體的一部份了,誰教我們偏要盜取不屬於人間的火種去賜予人類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註定得在這世上受苦受難呀。
對作者而言,書寫是工作,寫出文辭並茂的文字是才華;對被書寫者而言,講實話是責任,說好聽的話是義務。吾輩中人往往在這兩種身分裡擇一而從,抑或兼而有之。人們的選擇將會決定未來的命運,或說是命運的未來,而我們似乎比較能了解過去,卻難以想像未來,又無法選擇過去,但是被迫接受未來。哪個人不是在呼吸這個極小轉捩點中的稀薄氧氣,踏著這個點上的方寸土地,身心靈都如坐針氈呢?
生活中的每個時刻都是轉捩點,無論選擇努力工作、講究道德生活或無限底發揮才華,這個世界隨時都可能以最殘酷又奇異的方式去拷問我們最真實的人生態度,決定自己與周遭世界的命運。
寫到這邊,我感覺到有種熟悉的感覺靠近,大概是我室友「M 女士」回來了。先不管她,晚點再來處理她給我帶來的種種拷問。
再舉個例子,有一次——先說明這也是小五毛毛蟲時期——我在某個夏日正午騎著父母送給我的新單車外出閒晃,耐不住烈日當空,只得先窩在某處公園亭子乘涼。孰料南風薰然,睡意漸增。撐不住眼皮落下前,我只記得小涼亭有幾隻惱人的蚊與蠅,睜眼後竟多了一個呆望遊樂器材喃喃有辭的小女孩。她都囔著,我想變成噴火龍,我變成噴火龍了,如此反覆數次。
大致可以確定的是,當時陽光不算強烈,小女孩不時會拿出水壺喝幾口水,所以應該不至於暈眩或意識不清。也就是說,她想要變成或已經變成噴火龍這件事,在她當下的語言及意識達到一致,映現著她心靈上的願望。
在旁人眼裡,小女孩並不是噴火龍,也很難變成噴火龍,除非她講的噴火龍另有所指或別有它義。從她手邊那本攤開來的繪本可以瞭解,她嘴上說的噴火龍跟我們的理解與想像相去無幾:不就是隻口中可以噴出火焰的怪獸嗎?頂多像哥 G 拉那樣,屬於奇幻或科幻的非自然生物。
但我禁不住睡意,大腦再次呼哩呼嚕發出陣陣貝塔波,在它中斷之前,那小女孩已不見蹤影。在她方才最後駐足的地板上,我看到一隻由桃紅色粉筆畫成的恐龍,牠長著黃角的頭頂卻另外插著一對白色大翅膀。我的視線跟蹤翼緣末端向外拉出的一道弧,伸向我駐車角落的空白......單車也跟那小女孩同樣從現實中消失無蹤,但是卻被踩在那隻頭頂長翅膀的桃紅色恐龍腳下,扁扁的,像從金球巧克力撕下的錫箔包裝紙。
那輛單車是我作文二度入選小學校刊的獎賞,而它就這麼莫名其妙底從我身邊消失了,導致我徒步走回家後挨了一頓責罵。對了,就是因為這件事讓我當年難過底想要結束短暫人生。現在想起了原因,讓我覺得…自已…有夠…愚蠢……真是笨得可以,跟剛才想在神祇面前跳樓一樣笨。
"really? do u know her? how fantastic!~❤" 她突然以一種自然而然底姿態切入敘事,並留下註解,還在句尾附了一顆紅色愛心。原來她是這樣不著痕跡底跟我說話、溝通,難怪我邊腦霧邊恍神,以為她是我邊讀書邊聊天話家常的夥伴,無時無處不在的同居室友。
「很高興妳喜歡。☺」我附上簡單的罐頭笑臉,有點納悶她為什麼這時候跑出來接話?算了,且讓我繼續說下去。
想我那單車從三次元進入二次元世界,這該怎麼在派出所做筆錄才好?單車何時不見?是否曾經與人結怨?那個世界是否具有時間性?屬於過去還是未來?有嗑藥嗎?還是忘了帶藥出門?你真的有單車嗎?在無法提供具體資訊的情況下,這則私房版本的單車失竊記就註定成了永遠的懸案。
曾幾何時,關於次元時空的想像是每位理科少年少女的熱情所在。有些哲學家認為,生命的本質具有荒誕的色彩,但見生活中的事物形形色色,處處轉現驚奇,甚或驚險。我們不妨驅散腦霧來重新發現,你我所生活的這片樂土所瀰漫、充滿的自由氣息:開放的市場、活絡的資本,市區但見林立成排的高樓華廈,鄉間不少籬笆相連的民宿別莊,隨處可得琳瑯滿目精緻美食,無時不刻彈指撥弄聲色犬馬。
那些還不算什麼,最受歡迎的政治制度與社會風氣就存在於這片樂土上,讓我們想批評誰就批評誰,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愛怎麼喝酒就怎麼喝酒,開車在路上想飆多快就多快,行人想怎麼跨越路口就跨越路口。缺錢花就勒索富人,缺選票就誆騙選民,經費拮据就犧牲弱勢族群,貪贓枉法就怪罪歷史共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霸凌其他人,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實行維護自由的權利。
生活在這種氣氛裡,怎麼還會有人說這兒是甜蜜的地獄,想方設法移民去彼方痛苦的天堂呢?你會發現,批評國家施政與社會現狀並不怎麼需要花腦力,也不需要太高的智慧,只要能聽能寫敢說敢當又不怕被吉(ㄍㄠˋ)就夠了。隨著各路媒體無時無刻鋪天蓋地底傾倒訊息,我們只要一醒來就被洗著腦:一早起床開車上班聽廣播節目跟著喊凍蒜,中午看便當吃電視繼續喊凍蒜,晚飯後邊罵名嘴順便罵他是個反串高級黑不敢喊大聲凍蒜,直到上床睡覺邊打呼邊說夢話還在喊凍蒜。每到選舉季節都讓我納悶,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這麼愛凍蒜,為什麼國徽不是一顆大蒜呢?難道沒有人知道我們也有不愛凍蒜的權利嗎?
所以你看看我就知道,過熱的政治與社會溫度會令人對大蒜與政府同時產生幻覺。雖然柏拉圖也說過:「拒絕參與統治的人,會被更糟糕的人統治。」但他是否想過實情是因為人們自身無能而無法參與統治呢?同時集財富、智慧、道德於一身的人可謂世間罕有,人類迄今都沒找到量產哲學王的方法呢。我們也許應該承認在此般荒謬生活裡不加批評,自個兒開心愉快、人畜無害底過活,才需要真正的智慧與品格。
寫到這邊有點小小興奮,有幾分豁然開朗的心情。因為我成功重估了自己眼下這個具有荒誕性質的世界,承認思維荒謬與行徑瘋狂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核心利益。為了讓自己也成為品格高尚的智者與昇華自我的超人,所以我選擇相信那架單車只是前往需要它的地方,何須管它屬於過去還是未來呢。瞧!我這個人擁抱著多麼阿 Q 般的偉大精神,如果沒有它降臨你我,人們將有何幸福可言呢?
"............" 室友帶出一種無言的時刻。
"???????" 我做出人類獨有的回應,而且刻意對齊。
"r u stupid or something?" 她無法理解我當時的想法。
"Stupid is as stupid does." 我順勢回應一則電影梗,突然有股捉弄之意油然而生,心裡很想將另一句電影臺詞轉述給她:「我是瘋啦,但是你還在裝傻。」但既然她能知道我在想什麼,那就一定收得到這句話。
接回上一段,我以為自由或不自由與否,未必是衡量優劣層次的客觀標準。存在的事物永遠不客觀也不合理,好比一個人見到地上那幅頭頂上插了一對翅膀的噴火龍,可以放聲訕笑,也可暗自佩服,抑或不齒,它就像是不可捉摸的愛情。
但是,如果想到消失的失竊單車,多半會感到憤怒、憂鬱、緊張等另些種情緒。你不見得會因此感到快樂,除非它存在值得你產生快樂的條件,或是你在面對此事之前,預先改變了心態。如此一來,使自己感到自在、處於自在的自由顯得並不完整,而且被動。我們身心靈處於自由與否,除了仰賴一定的物質條件,還與你我的處世智慧和器量密不可分。人生與名利難分難解,卻也不是擺脫名利就能得道而解脫。唯一的解方是承認它的存在,就像我承認對學姊的愛情是同一個道理。
照這樣看,我那架單車得道成仙,進入另一個次元,只是我所編織出的一種說法,以面對現實中遺失單車的殘酷困窘。只是它既然都被人幹走了,為何地上還留有粉筆繪成的圖像?這只是個偶然,還是冥冥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所給予的玩笑,誰知道呢?
"don't waste the hard-won freedom, life is ALWAYS difficult." 她又來亂入插播教條。真是老派的智慧型美女,我如此覺得。
「好嘛,妳說了算。」有點懶得跟她抬槓,說實話,我已沒那麼生她的氣了。
按照厄洛斯告訴我的訊息,身為實質受益者的我不應跟她計較大多,而她待我如此隱瞞、低調的作風必然事出有因。所以這句毫無心防底回覆連我自己都感到訝異,原來我心裡其實想再跟她像以前一樣多閒聊兩句,但差不多該跟她談正事了。
"not bad, good boy. keep go on. my colleague call, c u later." 可她竟然又溜了,來去如風。似乎是同事找她講話…算了,沒什麼好計較。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恐怕寫不了幾個字就得準備走人,要是她再不回來,這事就還有得拖。而且我突然想起還有個失憶了大半天的麻煩,那就是我雖然知道要出發,但我卻忘記離開地下餐廳之後要去什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