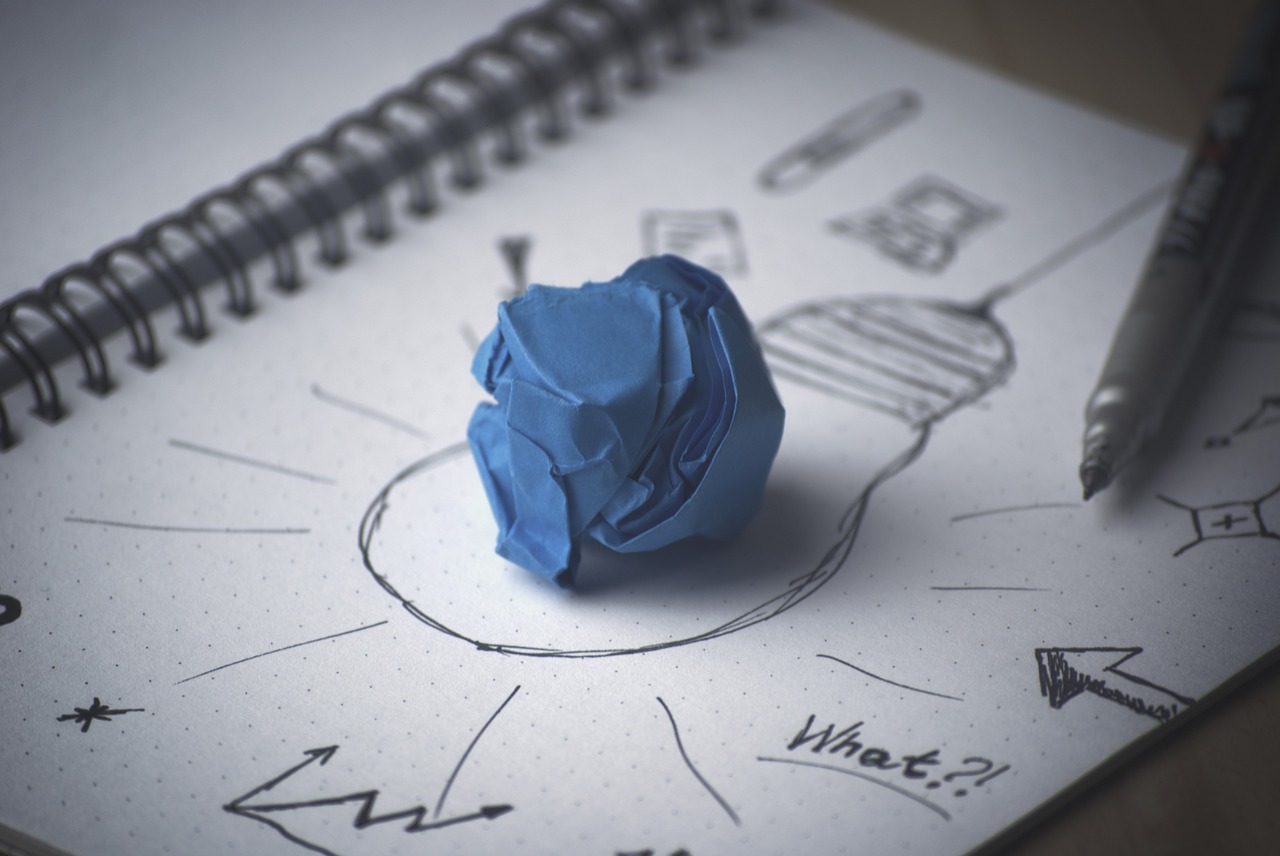一九八九年七月,在一次「猛浪譚」的特別節目中,貝爾納.畢佛特地移駕到美國的史丹福大學,訪問兩位在美國任教的法國大哲學家:您本人及荷內.吉拉爾。當您被問到自己與吉拉爾的區別時,您用兩種類型思想家之間的區分來回答:狐狸和野豬。可否請您解釋這項區別?
是的,這個觀察來自西元前七世紀的詩人阿爾基羅庫 (Archiloque) ,他說狐狸懂得許多招數,而刺蝟雖只會一種戰略,卻是非常有效的戰略:牠會蜷縮成一團。思想家可分為兩類,這種觀念後來又被拉脫維亞哲學家以撒.柏林 (Isaiah Berlin) 發揚光大。我同意這個看法,但我自己想像了一個小變化,把刺蝟換成野豬。
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荷內.吉拉爾這類思想家,他們一輩子深掘一個相同的觀念,用野豬比喻比用刺蝟傳神。所以,一邊是野豬型 (或刺蝟型) 思想家,他們孜孜不倦地來回同一條羊腸小徑,終於能夠為他們念茲在茲的難題命名,然後不斷定義它,一次比一次精確。荷內.吉拉爾本人認為,人生苦短,連一個觀念也難以淋漓盡致地發展。然後,有些思想家如我,幾乎到處都去探索。我們是狐狸型思想家,一開始就往旁側發展,然後逐漸擴大探索範圍,雖然不一定總能做到,但有時也能綜合他們所有的研究成果,做出結論。我自認是狐狸型思想家。我的本性如此,別無他法,只懂得盡力到處遊走,跟泛托普一樣。不過我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為什麼身為狐狸會讓您付出昂貴的代價?
因為我從來不被當成任何領域或任何問題的專家看待。另外更因為沒有任何概念與我的名字相連。我不代表那個被視為某些哲學家的發現而連在他們名字之後的觀念:伊比鳩魯的偏斜、笛卡兒的蜜蠟、盧梭的公共意志 (volonté générale) 、梅洛龐蒂的肉身、德希達的解構、荷內.吉拉爾的模仿理論等等。
我沒有標誌,沒有品牌。然而,沒有標誌的哲學思想無法傳播。我的作品比較像萊布尼茲的作品。這位《單子論》的作者,到了晚年,試圖為自己綜論總結時,覺得彷彿面對著一片遼闊的水域,有人在裡面擲入了幾顆石頭:每一顆皆激起一圈圈漣漪,互相交錯卻又各自完好。這一個整體有如一片恆動不息的流動森林。我認為自己的作品有點類似這種意象。
即使這些探索並未產生「標誌」,卻也萌生出許多概念:歸零姿勢,博學第三者,自然契約等等。不僅如此,這些概念都化身成人物,許許多多的人物……
我的確覺得被這些人物穿越。我是一大批軍團。我是誰?我是航海人、哲學家、作家;但也是荷米斯、初成人、博學第三者、敘事人等等。引用菲利普.德司寇拉的專長領域來說,我的神智以「類比推理」的方式運行:它不斷自我投射到差異之中,綜覽生物與事物無窮無盡的多元性。
《禮讚法文哲學》 (L’éloge de la philosophie en langue française) 這本書──您用它來介紹您所指導的巨型計畫《法文哲學作品庫》──,書中寫道:「所以,請別訝異:法文哲學,至今,在賦予它語言的這個國度本身之中,仍苦陷遭荒廢棄置的窘境,其實它已成為一門被排除在外的哲學。」然而我們清楚感覺到:您將法文哲學描述成一名「自由又孤獨的工人」,這樣的形象其實就是您自身的寫照。此外,您也並不避諱,總覺得自己被知識圈排除,擠到邊緣。這有什麼根據呢?
首先根據我的治學方式很早就不被哲學主流派認可這個事實。法國境內,在各種教授哲學的場所,所教的比較是哲學史,而非哲學。老師教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樣很好,我沒有任何批評的意思;不過,到了某個時候,會覺得似乎出現了一種奇怪的循環:只有擅長評論的人才能成為教授,然後他們重新教學生如何做評論,以後這批學生又繼續教授評論之道,依此類推。這造成一種哲學言論的自我封閉,很早就讓我感到窒息。當然,沒有比閱讀偉大經典更有效的養成方式,但到了某個程度,應該脫離這個循環,試著用哲學的方式思考,也就是說,創新,找到新意。
然而,事實是,在科學與哲學,我的兩項學養領域中,我都遭遇難關。在科學方面,我遇上一連串重大創新:從新數學到訊息理論,另外還有當時正在生成的DNA化學。在我那個年代,一位科學系所教授的授課內容中,他自己在大學所學到的部分,僅佔極少的比例。他會不斷遇到本門科系的更新。然而,在哲學方面,我看到的是一位老師,跟作評論的原則一樣,可能把他曾在大學課堂上學到的內容,百分之百移植到他現在的教學中,只是將評論的核心範圍定義得更精細。過了一定的時間後,我發現這個循環應該總有終止之時。
所以,我的雙重學養使我處於失衡的狀態。再加上學術界的環境艱辛:當時我必須為我的哲學博士論文答辯,因為我的指導教授半途放棄了我。在我的學術生涯剛起步時,我是被哲學界排擠的邊緣人。給我的職務都不是我的專業領域。這些來自個人、學界和知識界的因素整體加起來,導致我決定爭取自由。該盡的義務我都盡了。如我先前已經說過的,我開始「自給自足」。
既然被體制排除在外,我便自營「米榭.塞荷」這塊招牌。而我必須說,我經營得還不錯。到頭來,反而是遭遇排外讓我獲得成功。容我補充一下:這樣的邊緣求生歷程──我是在主編《法文哲學作品庫》時才知道的──,其實是許多法文哲學家都走過的路。德國和英國哲學家幾乎全部都是教授,在法國則極少哲學家得以出任。必須等到第三共和時期,柏格森和阿蘭 (Alain) 才當上哲學教授。不過在那之前,法文哲學家並不認為自己像個教授,反而比較接近思想家或作家……
如果哲學不該簡化成與昔日經典作者的辯證,您會如何定義它?是一項發明創新的研究嗎?
仔細檢視這段歷史發展,我們會發現,亞里斯多德預見了中古世紀,正如柏拉圖預見文藝復興,如笛卡兒預見現代時期。對哲學而言,這有什麼意義?意義是哲學中有些類似預期的部分。在我看來,那正是哲學的原動力。哲學的工作在於預想。一位哲學家之所以被認可,所依據的是他曾預先掌握某種根本之事,而且後來成真。思考即是預先掌握!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之書摘,選自 塞荷, 米榭., 勒葛侯 馬當., & 歐托力 斯文.
(2019). 米榭•塞荷的泛托邦:從溝通信使荷米斯到一手掌握世界的拇指姑娘,法國當代哲學大師的跨界預見.
, pp. 389 - 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