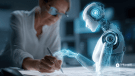搔起頭,絞出腦汁,努力想記起自己等一下要去的地點,卻從腦海底下的礦脈挖掘出自己曾在多年以前所做的一場夢。
夢中的我假冒成律師去探監,獄卒不疑有他,飛快底領我往地下室方向走,一連跳下好幾層樓才抵達會客區。獄卒每往下層跳躍一次,我也只得跟著跳。是的,「跳下」,別問我為什麼,這可能跟一九九七年沈船電影劇情中的男女主角對白有關,但也有可能只是做夢的人太緊張。
最後我在層層深掘禁錮的明亮房間見到委託人——一位相貌與自己對稱雷同的女人,她在牆上的鏡子裡面注視著鏡外的我。同時令我吃驚的是,這個地方一點都不像冷冷黑牢,比較像是 AI 產業文宣裡的前衛高科技辦公室,連空氣都是清新得不得了,完全沒有地下碉堡或礦坑那種帶著凝滯、潮濕又混濁油煙的恐怖氣味。
為什麼我要來到這裡?一路飛奔早已讓我忘掉來此的目的,還是說,就是因為鏡中女子想要看我?她的凝視令我感到一陣驚懼,沒過多久就在渾身冷顫的感覺裡甦醒了,現實中的小腿上下關節同時冒出新鮮疼痛。這場夢簡短得挺標準,雖然夢境中的我還沒返回地上,但我可能是在跟那個「我」相互見面。如果這夢有後續,我希望能直接快轉跳樓梯的部份。
如果她就是「我」,她為什麼要見我?還有,明明我是位身上帶有 Y 染色體的男人,那個「我」為什麼是個女人?另外一件怪事,她為什麼待在鏡中?「我」眼中的我,被凝視著的我,是何模樣?她看到了什麼?想看見什麼?又有什麼預期出乎於她的想像與觀看?我的形象是表象,「我」對我的凝視能否穿透?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也許那不是「我」,只是一面虛構的鏡子,從中虛擬出一個想像的自我形象,好讓我懼怕,讓我記得自己應該是誰,想起自己並不是自己眼中的自己。
若不是要我從現象中看見本質,或許對它就不值得探究,那是場夢,我可以當它是潛意識演給自己看的自娛小劇場。時過境遷,它所發生的年代與背景都已喪失,我真的忘記了它與時事前後脈絡的關聯線索。多年後拿它對照網路上各種經過簡單演算隨機亂跳出來的不知名解夢文,神奇 AI 告訴我那場夢境罕見底揭露了我內心對神祕事物的渴望。但是大多數求神問卜、對夢境好奇而上門的訪客就是想解讀出自冥冥之中妙不可言的神祕訊息,所以那不是廢話嗎?
的確,我只知道觀察人際之間的際遇,卻從沒想過會遇見自己。在此刻想起了這件事,細數過去無時無刻的浮想聯翩,難道不是某個自己身上帶著的神秘力量所給出的生命拷問?
如果揣摩我那假室友的想法,我想她會這樣告訴我:「當人們拉扯不動自己的人生,或許應當把自己交給命運,或是生活中的偶然與不可預知,它會將人們整出自己應當如此的模樣。」
因為自己的態度、選擇、決定與際遇無一不與自己面臨的命運息息相關,無論是順其自然或刻意營造,最後都會回到自己身上。
命運只是後設的解釋,雖然人類無論如何都會不由自主底為自己的人生找出因果關係,我們依然可以調控莫比烏斯帶的長短、寬扁,甚至是裡頭的色彩,當然也可以多旋轉幾圈、與他人的環帶相連,類似基因螺旋那樣。
那我懂了,因為我是哺乳動物性別系統中 XY 性染色體的組合,我有一半的「我」是她。「我」在我身體中沉默著,觀看自己所思所行,始終記得我曾經歷的事物,在夜裡收拾我在白日裡闖蕩過的生活,記錄那些有趣且多情的人事物。
「我」想念她,「我」要我別忘記那個和她擁有同樣 X 性染色體的人,「我」要我去想起她。我現在知道了,「我」從來都沒有接受我當時的決定,但是「我」被阻隔在鏡中,莫可奈何。
我對「我」感到歉疚,然而我當時也無可奈何。
理想的情況是,人們應作出令自己滿意的所有決定,要接受自己不會後悔的最佳與唯一選擇,這樣即使遇上再大的痛苦與悲傷,都會迎接自己註定擁有的幸福快樂,成為真實的自己。
實際的情況則是,地球上從來沒有自然形成的莫比烏斯帶,它得要靠人類去製作而成。雖然它是個徹頭徹尾的人造物、人工產物,可是,我們不就是透過它而瞭解到許多世上難以捉摸的事物與概念嗎?
故事將近尾聲,我現在認為人生可以視為一段學習「何謂笑」與「如何笑」的旅程:笑便是笑,或不是笑,乃至不笑之笑,笑不以笑,不以笑之為笑,是謂之笑。
每個人的生活必然都存在苦悶,甚至充滿痛苦煎熬,但是別放棄孤芳自賞,請你笑一個給自己看吧。承認世上的形色荒謬與各種不如意或許無濟於事,但如果連你自己都不關愛、照顧自己,又有誰會來愛你呢?
"hahaha, it's fun, so interesting. " 假室友終於回來了,敢情是刻意要壓軸耍大牌?
「謝啦…既然妳出現了,妳還打算隱藏多久呢?一個人從來就不只是一個人,所以妳就是妳們。遠從世上還有噴火龍的時代就存在至今日,神話傳說中三位一體的九姊妹們,各位奧林帕斯國際集團的文化事業部小編群,差不多該結束這種不透明的對話了吧。」我開門見山底說。
"have u finished ur job? " 她們先問我書寫狀況。
「算是吧,還差幾句。欸,妳們別再繞圈子講話了,省點時間力氣吧。」我算是鬆了口氣,其實這個故事不能沒有她。
「sure……你已經確定我們的身分了嗎?」
「當然確定……妳們是傳說中的公主䥸䝟䳮䟑䎘䫱䉷䰯䕈䟐䬝吧?」
「哈哈,別鬧了……其實我們是巨龍㱎䖘䵈䶁䘔䶑䘓鋱䩳䵷㒪䪉䉥。」
「那妳們還跟著我起鬨……真是夠了,時間有限,我可以開始提問了沒?」還是早點進入正題比較好。
「只限於我們能回答的內容。」
「誰理妳呀……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妳們明明不需要特定語言就能跟我溝通,為什麼一直跟我講外語?還有,妳們是用什麼方法跟我進行對話?心電感應嗎?妳們是怎麼讓我聽得到或聽不到聲音?」
「這不難吧?我們只需默禱就能溝通,也能選擇要讓誰聽到我們講話。至於刻意使用外語的原因,一來是避免被旁人竊聽,其次是利用不同的語言邏輯,讓你專心聽我們講。另外,我們有辦法讓你陷入沉思,使你身處的時空停滯下來,你就能不受外界訊息干擾,自然聽不到聲音。」
「竊聽?太瞎了吧…妳們講的內容不是都被厄洛斯聽到了嗎?」要我相信她的解釋有點困難。
「應該沒有。他本來就帶人在附近找機會狙擊你,所以你飯後打瞌睡時才會做夢,否則短暫的瞌睡一般不會進入夢境。我們本來怕你真的睡著,想把你踢得清醒一點別入睡,但一點效果都沒有,還好最後是你不曉得因為什麼事把自己驚醒。厄洛斯是發現我們跑去請大姐大當救兵後才趕緊要把你帶走,他們幾個男神對付不了她。摩依賴的王牌大姐大可不是叫假的。」
「踢?所以從白煙裡噴出來的那個足印是……所以妳們跟厄洛斯的委託人沒有關係嗎?」
「基本上沒有。繞開記憶去提取意識感受,這與設置夢境是不同的情況,會彼此妨礙,導致失序與混亂,所以我們雙方原則上無法合作。我們原先是只讓你忘記帶筆電出門,引導你在專心與清醒的狀態下去回憶往事,在強制沉浸書寫的過程中療癒自我。他們則是一直想讓你睡著,把你帶進安排好的夢裡才能安全、有效率底完成他們所接受的委託。雖然我們知道那位委託者的身分,但是我們另外曉得一些關鍵。」
「所以我今天灌了這麼多高單位咖啡因,卻依然在夢境與意識中像個鬼魂似的遊蕩,原來就是被妳們兩批人馬給輪流折磨啊!」我感到無奈又懊惱,但歸根究柢也都是我自己的問題。
「不至於折磨吧?沒人逼你喝唷。」
「也對啦,妳們剛才說的關鍵是指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呵呵…拜託我們呀~剛剛有人很兇,一點都不溫柔體貼哩。而且我們每個都是生過小孩的歐巴桑,恐怕幫不了忙耶,真遺憾哪。」她們竟然給我拿翹。
「哎唷~那只是個小小小小的小誤會,都是我的錯。九位美麗又善良的姑娘啊,請您們大人大量,大發慈悲原諒我這愚蠢凡人的無禮之舉。拜託~拜託~」
「哈哈哈,這種態度太明顯了,靈活有餘但誠意不足,算你零分。改天你來報名我們集團的話術訓練吧。」
「嗯啊,我正有此意。可是能否請您們先告訴我,為什麼我夫人去求阿芙蘿黛蒂?」
「嗯,其實是你自己捅的簍子,你應該不知道吧?」
「我?我怎麼會叫她去拜託神祇把我自己射死啊?」
「我們只知道大致的原因,不清楚他們會如何進行。最近有幾次夜裡,你邊打呼邊做夢。結果那個你所看不見的自己跑出來說夢話,陸陸續續重複幾個關鍵詞與人名,大概都被她聽到了。」
「什麼關鍵詞與人名?妳們跟另一個我有接觸過嗎?」
「沒有,另一個你無法溝通,我們只能聽他講話。至於講了什麼關鍵人名……」,她們稍微遲疑了一下才說,「答案應該是你自己最清楚。」
那應該不是我講的,是那個「我」講的才對。為什麼「我」要講出來讓夫人聽到呢?這分明就是整我自己呀!但是經過早先那番反省,我可以理解「我」會這麼做的原因。
「嗯,我瞭解了…那她應該不怎麼開心,我沒被趕去睡沙發跟跪主機板算是很走運了。」
「是嗎?這裡才是最不合理的地方。」她們繼續推論:「如果你家夫人真的生你的氣,想報復你或那個女人,就應該去向維護婚姻與家庭的赫拉或其他復仇女神祈禱。但是她沒有這麼做,而是去找專司愛與美的阿芙蘿黛蒂,你有想過這是為什麼嗎?」
我停下來思考片刻,找到了答案。
「因為她想重新喚起我跟她之間的愛情。」我說。
「不錯嘛,你這人還不算太笨。」接著說:「我們一致認為,你家夫人雖然心有不甘,但是她包容了你和那個女人的過去,陪你承受悲傷並且守護著你,在寒冷的夜裡給你溫暖,確確實實底成為你當前生命中絕對無法割捨的重要部分。她對你懷抱的愛意雖然平凡,卻也十分偉大。每個存有的生命歷程都有缺陷,必須相互給予關愛才能圓滿。」
我接不上話,但同意她們的見解,內心覺得矛盾又沮喪。
因為心懷怨憤,感嘆生不逢時,我常常抱怨這個世界,以為批評缺失就是負起當前所能交差的義務,早將自己的存在價值壓得比日式和紙還更扁更薄,以為被任何人踐踏也不會感到痛苦。但即使如此,夙夜輕風吹拂零星雨露,三三兩兩落在我瀕臨乾涸枯竭的心湖,點滴都彌足珍貴。我仍接受著這個世界的滋養。
縱然不免落寞、寂寥,但我依然能為這世界給出些許美好的幸福與樂趣。即使只是為旁人倒杯水,幫家人蓋被子,在小小外星人面前扮個故作幽默小丑,為認識與不認識的年輕人提供建設性意見,也能夠創造出不輸給恆星的溫暖。
生存有苦有樂,若說「他人即地獄」,那也會是天堂。端看我們自己怎麼想。
「好吧。來解釋一下妳們對我的義務究竟是什麼?」我換個話題讓對話繼續下去。「妳們說很早就出現在我身邊?是有多早?」
「早在你曾想永遠睡著的那段幼蟲期,從此就成為需要神明眷顧的對象。根據你的個人潛力與性格,我們被選來看顧與觀察你,調查你在童年階段為什麼會思考自殺與生命,當時也曾經親眼去看過你一次,就在公園的涼亭。」
「…………」我無言。
「呵呵。」她們倒覺得有趣。
「所以我那輛腳踏車跑去哪兒了?」
「不要問,很恐怖。真想知道的話,借你剛才寫下的文字來講:『機器就是機器,在那種環境下很難維修與回收。它們的命運從一降生就被決定』。總之,最後就是一片廢鐵。」
「我才第一次騎出門,妳們就毀了它?」
「說來話長,有機會再講。」
「妳們不覺得歉疚嗎?要怎麼補償我?」
「只有人類有良知,神祇可沒有唷,嘻嘻。再說,我們來看顧你,你本來就該給我們一些供品才對吧?!」
「咳,不跟妳們計較。妳們對我很了解,連學姊的事情也知道,可是在我的記憶裡,我與妳們相互對話的時間又沒那麼早。如果一開始保持沉默,後來為何又要開口?」
「青春期的你太敏感又太無知,又不通外語,讀到大學還宅得連妖精打架都不懂。萬一你在人群面前經常表現出喃喃自語的樣子,大概這輩子就被我們毀了。」
「所以妳們在我需要思考與寫作的時候才開始跟我講話,還影響記憶內容給我洗腦…這就是妳們的手段?」
「你總算開竅了,但你自己記性差也不能全怪我們。」她們接著說:「該忘掉的偏不忘,該記得的卻老是記不住。人類若繼續把日常生活交給智慧型工具,天天依賴它們,遲早會淘空自己的頭腦。建議你該快點戒掉它們才不會提早失智。」
「哼,我倒認為自己之所以會這麼憤世嫉俗,妳們也有不可逃脫的責任。不就是妳們透過對話來教育、影響我,讓我提出各種 low 到家的看法來嗎?」
「這樣講有失公允唷。後來你學到的知識、懂得的事情都增加不少,才能形塑出自己的見解,繼而接受我們的存在,萬一我們的身分被你猜出來也比較不必擔心。現在不就是嗎?你沒有大聲嚷嚷說這世界有看不見的存在者,仍有許多一般人無法察覺的事物在默默運作,表示你承認了存在者都須遵守的宇宙法則。」
「妳們的意思是神祇也是類如凡人一樣的存在?」
「大致沒錯,主要差別在於存在狀態不同。神祇也有生死,也有力所難及的時刻,也要面對自己的存在意義與價值,會涅槃也要輪迴。或許你以後會有機會再多了解一些。」
「我有點好奇,凡人會成為神祇嗎?」
「這不是我們能回答的問題。但即使有辦法,你也未必想。」
「好吧,換個方式問。為什麼我會需要以及我能接受妳們的幫助?」
「這算什麼問題?因為你是凡人啊,而且還是個毛長齊了卻依然幼稚的老屁孩哩。嘻嘻。」
為什麼老是問錯問題啊,我真是……
「那只是陳述不夠精準…重問一次,為什麼我有資格接受妳們的幫助?」
「有許多詞彙可以互相詮釋這個情形,但簡單來說,就是你已開始覺醒,需要接受引導。如果你只是個每天渾渾噩噩過日子的凡人,就算我們再怎麼幫助你也是浪費時間。這樣的人永遠也不會發現我們的存在,更不可能與我們對話,甚至親眼看見我們出現。」
「所以關鍵在於我是否是個已覺醒的人?覺醒是指什麼?」
「對。覺醒也有許多種情況,例如通過感性的領悟與想像、理性的分析與演繹,以及結合兩者互為發明來得到解釋,這需要想像力。想像力的運用很微妙,不能過分拘束也不能太放縱。像你這類的覺醒者還只是很基本的準入門階段,許多能夠發揮的進階人士已稍微觸及到一些關於這個時空的本質,去發現生命體在宇宙間的運動,並且回饋於實際生活的運作中,享受生命,並燃起他人生存的希望。」
「妳們懂很多嘛,可是我認為自己不是理性論者也不是神棍。」
「放輕鬆點,老兄。凡事發自你的內心,去偽存真,順其自然,別再壓抑情感去扭曲自我,這樣你看事情就會有不一樣的眼光與感受。」
「又來說教,內容還跟厄洛斯講得差不多,妳們真是不論做什麼都不會令我感到無趣啊。」
「呵呵,因為那是當前心理諮商的 SOP 啊~這是個看似自由卻反而處處受到壓抑的時代,你懂的。好啦,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也該離線囉。」
「所以以後不會再有對話了?」
「倒不是這意思,但是我們已透過強制書寫與回憶去療癒、創造了一個新生與淨化後的你,驅除你心裡原先沉重的抑鬱與消極,接下來應該算是可以盡情發揮自我、激發出創造力的狀態。我們先前對於你的義務與責任都被解除,暫時沒有需要我們再為你做些什麼了。」
「那就沒人吵著我要聊天,搞不好會不適應呢。」
「還沒分開就想念我們啦?今天的情況比較特別一點……喔~原來如此。」
「什麼事情原來如此?」我覺得奇怪,她們為何欲言又止?
「那個沒什麼,不用介意。我們本來就還有其他人要照顧,也只有在特定時間跟你對話刺激出靈感。你還記得我們對話的那些時刻吧?」
「妳們是指睡前沉思、回憶與寫作的時候嗎?」
「有時我們真的很忙,你也可以藉由冥想、打坐來跟自己交談。別擔心有不好的東西出沒,它們都是你自己的意念,是另一些原來看不見的你。讓他們出來走動,或是聽他們自述,應該可以幫到你很多忙。」
「我會注意的,今天已經見識過她的能力了。」
「呵呵,對你自己好一點,每個人都不是只有『自己想像的自己』。你是個有趣的人,改天再來找你喝午茶、聊聊天,細節等我們敲好再通知,就先這樣說定囉~」她們接著說:「你也該在五分鐘內離開,這樣就能在搭上公車準時赴約。」
「赴約?妳們知道我要去哪邊嗎?」
「你果然全忘光了,真沒辦法……。我們剛剛想到,今天原來是你們夫妻倆開始交往的紀念日,你們昨晚睡前約好要一塊去有戶外陽光的庭園餐廳喝下午茶。」
「啊!對吼!」
「看她多掛記你呀~誰教那個看不見的你管不住嘴巴,哈哈。不過嘛…念在你今天沒白混,稿子還算寫了不少字,我們就好人做到底,特別再給點『殺必死』提醒你。等一下你們約會時,如果看到有位穿著很潮又神情狐媚的黑褐色頭髮男妖精在你們附近出沒,別去看他,也別管他要做什麼。」
「為什麼?」我有點訝異,連忙追問:「難不成他還要再用弓箭射我啊?」
「那可是你自己講的,我們只是推測而已,不保證發生。因為你們夫妻倆今天排了午茶約會,所以厄洛斯他們一定也在趕時間完成委託。雖然不清楚細節,他們應該只算達成了一半任務,畢竟你已經變回一身清爽模樣,這可是你妻子最盼望的奇蹟之一……可惜衣服不大合身,嘻嘻。但是話說回來,大姐大剛才回報成果時偷偷告訴我們,說你未來的表定命運中還有個女兒,然後再胖回來。」
不會吧?!我又在腦中大喊。連根驗孕棒的影子都沒見著,突如其來的命運預告實在太令人震撼了。但我已經在構思這位前世情人的外文名字該走哪種氣質路線好,選什麼第二專長跟第三外語,又該怎麼省吃儉用存錢讓她去那些國家留學,出社會以後如何勸她去做 NGO 對抗體制還是要混進資本市場吸黑心財團的血……喂!這到底是什麼情形?! 為什麼我還會胖回去呀?!
「信不信由你囉,這不屬於我們的業務範圍,所知有限,其中應該還有許多因緣得靠你自己去串連。成或不成,編織未來命運的紡線都在你身上。」
「嗯,這些我都懂得。那…為什麼我還會發胖?」我真的很想知道原因。
「那就快上樓去搭車吧。幫了你這麼多忙,請我們的下午茶要選正統英式的喔,要記得訂可以容納十個人以上的海景包廂,跟氣質淑女約會別再選這種地下餐廳啦,還有千萬別帶老婆孩子來唷~」
妳們這群不食人間煙火的貴婦真是獅子大開口啊…而且完全不理會我的問題…但是我也很久沒喝正統英式午茶了,更沒去過海景包廂,利用這個機會見見世面也不錯,也許可以給自己增添一些靈感。
我好像開始對這個世界的日常生活有所期待,也許我真的被改變了。
「沒問題。」我發自內心由衷底說。
「改天見。」她們異口同聲底回答。
「謝謝妳,我親愛的女神們。」
「再會了,親愛的——————」
她們話還沒說完,此時從我長褲右後口袋傳來一陣震動,隱約有支歌曲傳來,可是音量非常小,還被周圍雜音干擾,讓我很難聽清楚歌詞。隨著聲音逐漸擴大,我聽到了其中幾個關鍵字,瞬間切換成瞠目結舌的表情。
「起來......起來……我們……的主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要創造…幸福…全靠我…自己!……」
Wa Cow!這不是我設定的來電鈴聲嗎?我明明就有帶手機出門呀!
兩千兩百公里外的大平洋南方小島上,在一間海邊小木屋的蜜月套房裡————
一名女子從浴室走出來,從容底在化妝台前坐下。她用裹在身體上的浴袍再次擦乾雙手,滑開手機接聽未接來電時的訪客留言。
第一則留言是公司同事丘秘書打來的越洋電話。她想或許發生了急事,否則公司一般不會在私人假期時還來電打擾。
「吳姐,我是 Peter。不好意思這時候還來打擾,我想知道妳審完那篇稿子沒有?剛才 M 女士主持完編輯會議有更新過修改建議,妳回國前有空可以稍微看一下。公司一切都好,沒什麼其它的事,祝妳玩得愉快。複審會議之前回覆妳的審查意見即可,就這樣。掰。」
第二通電話則顯示為 Peter Chiu 的私人來電,與第一通電話相差約半小時。
「嗯?哈囉~學姊妳還沒回到飯店嗎?算了,我偷偷跟妳講喔,其實剛剛老闆娘在會議上抱怨學長怎麼把她給寫進小說裡了,還寫得那麼兇惡…嗯,其實她有點生氣…還問我為什麼選她的形象寫個老太婆殺手,本來想直接叫他刪掉,但是她又覺得叫不動自己兒子,問我有沒有什麼辦法,這很明顯就是要我打電話給妳,要妳幫她搞定嘛。其實學長在小說裡也有寫我跟我男朋友呀,我們都覺得還挺有趣的說。嗯,反正我已經把指示傳達到了,剩下就妳們夫妻倆自己處理啦~別跟學長說是他媽媽的意思喔!先這樣啦,我去吃個飯,晚點再聯絡喔,記得要更新旅遊相簿給我們聞香唷。啾咪~掰掰!啊~~對了,老闆娘說晚上會帶底迪去吃大餐跟看兒童哲學劇場,晚點才會回家。以上,報告完畢。See you later 啦~」
聽完語音留言,女人閉著眼搖搖頭,擠出一絲無奈苦笑。她深吸口氣,覺得自己好不容易想盡辦法來到南洋小島二度蜜月,卻仍然被工作與家務事追著跑。
火熱豔陽斜斜底掛在這塊南太平洋島嶼的天空上,海風吹拂沿岸的棕櫚樹林。光線穿透小木屋窗簾,直射著這一片片柚木板組合而成的地板,明暗交錯的光影猶如琴鍵,敲動女子心裡的音符,讓它們帶走數分鐘前從遠方島國飄進房裡的紛紛擾擾。
她起身,哼首小曲默默獨舞,猶如一隻自在且輕盈的蝴蝶。
待她踏著舞步走近窗邊停下,向右拉走厚厚簾幕,開啟小木屋面海的那一大扇落地窗,視線能將兩百公尺外連綴至天邊的湛藍海景一覽無遺。
她一手撫著微微隆起的下腹部,就扶在窗邊陽台的柚木搖椅上緩緩坐下。微涼海風催促她裹緊浴袍,瞇起眼,望向遠方尋找那男人的熟悉身影。
陣陣白浪前仆後繼,一場持續了三十八億年的沖刷、流轉與匯集運動,這股孕育生命的力量仍在地球上踴躍著。
她的男人從大海破浪而出,赤裸身體,臉上戴著運動墨鏡,左手腕則環著一條琉璃串珠。彷彿呼應著她的凝視,他從浪潮起落的沙灘邊往她所在的方向走去。
比起親密的擁抱與接觸,凝視著那個走向自己的男人最能讓她心底湧現無比幸福的感覺。她始終記得當年他們第一次在圖書館大門旁的約會,她為了他的平安現身默默祝禱。
她淺淺底笑著,用只有自己聽得到的音量輕聲底對他說:
「歡迎回家,親愛的尤里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