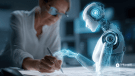餐後血糖緩升轉降,乍睏還醒,濃重睡意跌宕起伏,這會兒讀過的文字段落往往要費力個反覆幾次才能解意。
撞撞復跌跌,覓覓又尋尋,箋箋書頁晃過眼前,萬重方塊字堆砌成巍峨雄奇巨大迷宮。橫豎字林魅惑森森,孤影穿徑迂迴曲折,何處歸向是依?聲聲苦楚繚繞,淒淒慘慘戚戚。
幾度往返,文字又繞回到似曾相識的語林,尚待摸清的指符接下來又要帶領讀者走至哪個世界?
思緒跳踊之際突然豁然開朗,趕緊提筆錄下胸中迴響共鳴,搖晃鋼筆針尖來回給稿紙紋身,鐫刻辭藻既似古又若今,這興許就是傳說中的神來一筆?
前景看似撲朔迷離,一眨眼卻見柳暗花明,我好像清醒了,畢竟人總是睡著睡著就醒過來。
即使是誤解,但我認為睡醒與入睡的過程倒像是場夢,既非睡著時亦非醒著時出現的各種光怪陸離,而是無法想像的出入口:從「此」消失,自「彼」而出,形成一個雙向的通道。
它好比是架旋轉門或一座螺旋樓梯,連結某些個神秘之處的橋樑與小徑,有點像任意門或魔衣櫥,但也許更接近一座每個麻瓜都能踏上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你不可期然底走到那裡,永遠因為無法拒絕它的誘惑而走進它,在另一段人生中經歷奇幻荒謬又超現實的哀怒悲喜。
先別去管什麼莊周夢蝶還是什麼蝶夢莊周,你難道沒聽見有條毛毛蟲邊打鼾邊說夢話?還是說你就是那條毛毛蟲?
說到消失不見這檔事,讓我偷偷告訴你:我小時候曾有讓自己在世界上永遠消失的念頭,也就是說,我在幼蟲期曾經想過自殺這件事。
根據我寫給自己的歷史,這件事發生在我小學五年級左右的某個傍晚,我站在浴室門後無言怒吼,張大嘴唸唸有詞,卻一個字都不敢講出聲。這不表示我是躲在別人背後放砲的小孬孬,而是我仍舊依戀家庭生活的表現。
換個角度看,這或許只不過是小孩子對父母與威權的一種反抗形式,但它的危險之處卻是我拿自己僅有的1up生命作要挾。我似乎開始懂得生命是有價值的事物,但真的是這樣嗎?
從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屁孩來考慮,有限的生活經驗恐怕不足讓我懂得「何謂生命」與「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年幼的我對眼前人事的瞭解還過份底粗淺,不只是坐井觀天的變態兩棲生物,甚可說是不可語冰的夏蟲了。
顯而易見底,我小時候的生活其實──相對這世界上許多忙著求生存的孩子來說──很幸福,竟然有閒情逸致開始思考人生的大道理?畢竟是幼蟲期嘛。
隨著歷練稍廣、智慧漸增,我了解到凡事必須「先講求不傷身體再講求效果」,於是我終於曉得一個能夠保全性命又完全毀棄毛毛蟲人生的秘密方案,其實也不難,就是繼續化蛹度過青春期,最後努力變成蝴蝶就好了啊!
"have u wanted to commit suicide before? " 她不可置信底問道。雖然看不見表情,但勉強想像她滿臉訝異。
"how do u have this experience? " 不待我回答就接著追問,顯然勾起她的好奇心。
難道妳沒有童年嗎?這句話終究硬生生鎖在我的腦海裡,然後它就形諸文字放在這邊了。
中場休息時間近乎捲曲於餐桌的睏倦狀態,與此刻這副精神興奮模樣相去甚遠,彷彿自己依舊是巴望著老師立馬喊下課放學馬上一溜煙跑回家看卡通的小五生。
可你想想,周旋在幾冊厚紙磚疊起的要塞壁壘中,我所能逃脫的方向,是繼續低頭運筆刻字、飲水嗑咖啡、張望或偷瞄紙牆外的其他顧客,或者縮起脖子、閉眼壓抑膨脹的苦悶和鬱結,窩在自個兒角落拉高衣領靜靜繭居,像圍在不遠處大長桌旁用功 K 書準備學測的那群高三生一樣。
雖說是一群,經過我不專心工作底用心觀察後發現,這些學生其實是三兩成群外加幾個獨行俠的集合體。
從桌上參考書、穿著衣飾與飲料是否有一致處,以及有無交談與招呼,再到肢體動作是否親暱、彼此的人際距離與個人空間容受程度,可以達到「雖不中亦不遠矣」的簡單分類。
凝望一陣後,覺得眼前景象似如非洲大草原上的派對縮影,非洲象、水牛、河馬、長頸鹿、斑馬與各種大小羚羊圍在池塘或河邊飲水,準備為接下來的生存奮鬥,而我這隻鬣羊也該早點結束張望,回到書山上繼續苦修才是。
雖然忘了那則激勵成功的小寓言是怎麼說的,但經過提煉後的意義關乎生存法則:一早從大地上甦醒過來,羚羊知道自己必須比跑最快的獵豹還要更快,獵豹則必須快得能追上跑最慢的羚羊,日復一日在這個世界上演你死我活的競爭戲碼。
很少人不被這個道理撼動,繼而接受這個顆種子讓它在心田發芽,默認道德偽善掩蓋血淋淋的殘酷現實,以為文明社會充斥高度謊言。
但剝去食物鏈外衣與速食道德,你可曾想過這頭羚羊其實就是那頭獵豹?
從空白稿紙裁下一段完整直行,我將正反面做了半回反折,首尾對接,利用標籤貼紙黏齊,做成一條再也無法區別正反面的莫比烏斯帶 (Möbiusband)。
我用左手撐住它轉動,把它當成串珠用右手二指走格子,逐字逐句連續默讀過一遍平時慣常誦記的幾篇文字: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將〈詩篇 23: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禮運大同篇〉裝進無限迴圈的稿紙帶,前後耗時約數分鐘光景,我希望清醒時的焦慮不安能隨之散去,起觀涅槃於手掌心中一圈宇宙。
隨著餐廳播送輕盈悠揚的古琴樂曲,我捆起團團烏雲擲入虛空,只是冥冥之中是否真有它們的歸宿呢?還是我愚蠢可笑的一廂情願?
在餐廳消磨時間與紓壓有許多好方法,但我已用掉最方便的幾個,沒剩下什麼優質選擇。記得以前曾看過有人在餐廳吃完飯後邊與朋友聊天邊打毛線,氣定神閒底與背景相融且毫無違和,這個辦法令我此刻打從心底肅然起敬。
身為一位外表看似成人,但內心卻住了小屁孩的阿宅大叔,我考慮以後在背包裡也要準備一盒公仔模型與一把專業模型剪來打發無聊時光。
“now u should sing or dance here, try dancing Beegees like John Travolta. ABBA's dance music is also great.”她分明是來亂的,因為我剛才調侃過她的飲食觀及其它。
「好主意…妳先做一遍給我瞧瞧,然後我再考慮看看。」順著室友突如其來的直球回了一記於事無補的反手拍,她卻沉默了。
我反省自己是不是力道稍嫌過猛?但願沒有傷到這朵溫暖可愛的解語花。
不過我費了心思把憂鬱硬塞進無止盡的莫比烏斯宇宙,期待發生的變化卻微乎其微。心底湧現的莫名惆悵依然滿溢整張桌子,煩惱得數不出來手上這杯不知續了幾次的苦澀黑水。
仔細想想,人又何苦痛飲酒精與咖啡因來逃避或面對現實呢?若清醒時的人生充斥困擾與憂愁,睡眠就有令人無法抗拒的芬芳甘甜,無怪乎被一文錢逼急的英雄好漢們多半只能選擇走進永恆的睡眠。
時刻惦記著文章與論著進度雙雙落後,無奈只有每日翻閱的讀物小有堆疊。過眼他人寫下的話語,涓滴思慮卻止不住從筆尖流淌而盡,稿紙露出雪白美肌無言底嘲笑我有心無力,但你也明白那些嘔心瀝血吐出的偉大文字本身就令人難以下嚥。
富哲理的思想者曾告訴我說,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是全由一個人造成,這聽起來有點否定某種信仰,但在此刻多少有些受用,因為一個人從來就不只是一個人。
就像憂鬱機器貓不能沒有大智小頑童,死神小學生必須依賴沒力查甫郎,黑衣杯麵男的存在意義有勞滑稽闊嘴人等一竿子壞蛋興風作浪,而愛情的滋味也需要麵包才能細細品嘗。如果消滅邪惡是出於道德危機之需要,伸張正義又有何道德秩序之必要呢?
智者教我:有即無,無即有,有即億萬有,無即無盡無。所以你能想像莫比烏斯宇宙裡頭有什麼嗎?
我同時也好奇她是否有些想法,醞釀了幾分期待。
喧鬧中藏著萬籟俱寂的瞬間,她留下恍若隔世般的沉默,一個字也沒對我說。
這就是她的回答。
就在一滴淚珠即將跌進大海汪洋的剎那之際,我得到了沒有絲毫憂愁罣礙的安詳與和平。
沒有形影不離的聒絮喧囂,也沒有惱人氣味與迫近擁擠,我不在意身外事物的運動是快是慢、形象是美是醜,冷眼看著身旁進行著的人事物,端詳自己內心的驕傲優越與徬徨無助,成為一個只擁有自己的人。
寧靜的世界引導我專心細數眼下種種存有,交纏語文數理工具運行奇妙的思維飄蕩,彷彿與遊走在黑森林中的隱秘國王同行。
那國王注視著我,從不開口說話,因為翻譯無法精準底表述,語言就成了我們最初與最後的居所。我一直很想問他當年是拿什麼牌子的鋼筆寫下 Sein und Zeit?是照片裡那支 Kaweco 檯筆嗎?他笑了,留給我一句 "Und nur das Unsinnige kann widersinnig sein." 之後又走上滿是迷霧的林中路,好似仙人般底自在自存去了。
雖然他沒有正面回答,但也沒有否定這個常人看來荒誕愚蠢的無意義提問,他的堅毅眼神伴著彷如名畫蒙娜麗莎 (La Gioconda) 般的詭魅淺笑,或許暗示我有猜中墨水品牌?
有人說筆是文人的劍,那我覺得墨水或許就是文人的血,但如果你知道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曾拿什麼材料在牆上寫作,必然驚駭無已。古人文房有四寶,今人讀書寫作已不再是筆墨紙硯加書僮奉茶搧涼,而是文青筆電、混著泡泡珠珠的茶飲加上涼爽空調。
猶記得大學時代的期中、期末考試,才剛普及的影印機拯救了吾等背水一戰、無路可退的學生們。若是課餘時間和經濟條件許可,還可以加上錄音機,要是班級氣氛融洽又團結,每幾人各自成立小組負責分科筆記與歷屆考古題,全班差不多就可以高枕無憂等歐趴。
那曾是我們用 modem 數據機與 B.B.Call 連接的青春,在智慧型工具出現前還能溫存的些微小聰明與一丁點樂趣。
插播回憶帶我重新回到現實,但撇下煩惱又抓緊甜美感覺不放的雙手究竟握住了什麼呢?如果思考是存在的證明,煩惱憂愁就是生存的本質。
所以你認為我真的清醒了嗎?若是,我此刻清醒於何處呢?若非,此處時空又是如何困住我?
姑且試著抽絲剝繭,先跟我來還原眼前重新盛滿的伴讀血汗試試:豆品來自南美的研磨咖啡、從原料玉米(想當然爾是北美)加工而成的奶精、主要以本地甘蔗精製的白砂糖,好個三位一體的精神支柱,今天鐵定又超過華生醫師建議的飲用量。近世曾是西方上流人士才享受得起的飲料與糖分,正大光明底擺在深深困坐地下室餐廳的我眼前。
幾縷薰香撲鼻,滾燙湯液蒸騰,杯口肆無忌憚底揚起裊裊白煙,彷彿兩百年前即將出港的蒸氣郵輪煙囪,隨時準備讓我看著看著又重新發呆,前進夢中的新大陸。
飄逸升上的輕煙裡頭隱約形成幾條人影在左右搖曳,像是穿著薄紗的女子們隨著婉轉琴音翩然起舞。在一個單位長度的普朗克時間中,我好像看到煙霧裡有一雙眼睛也在看我,孰料白煙突然化為一只超大的五指足印倏地猛然噴向我臉。